你感染病毒了(四)
已阅读:754次
二月十五日
当我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发觉自己穿着外衣躺在被子里,手里还攥着一束白色的玫瑰花,样子有些滑稽,我起来洗了一个澡,才渐渐地清醒了回来。
我家里没有花瓶,我只能把玫瑰花插在平时放牙涮的茶杯里,倒有了些后现代的味道。
我仔细地回忆着昨晚每一个细节,想着ROSE的脸,还有她身上的那股气味,那股气味刺激了我的嗅觉器官,使我开始用自己的鼻子回忆起了另一个女孩。
香香。
我叫她香香。
ROSE的脸,长得和她一模一样。
从我第一眼见到ROSE起,我就又想起了香香,想起了她的脸,她的气味。
我叫她香香,因为她天生就有香味,从她的身体里散发出来的香味。
我能用自己的鼻子在一万个人中分辨出香香来,我发誓。
但这再也不可能了,因为,香香已经死了。
她死的时候,只有十八岁。
我想她。
在那个夏天,炎热干燥的夏天,副热带高气压控制着我们的城市,连坐在家里都会出一身大汗。香香是我的同学,我们班级还有其他十几个人,除了林树以外,我们全都报名参加了一个三日游的野营,去了江苏的一个海边小镇,据说那里非常凉爽。
坐了五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和轮渡,我们达到了一片广阔无边的芦苇荡。那儿有大片的水塘和泥沼,长满了比人还高得多的青色芦苇,范围有上千亩大。一旦你躲在其中某个地方,密密麻麻的芦苇足够把你隐藏,谁都无法找到你。我们就在芦苇荡中间的一片干燥的空地里扎下了营,搭起了两个大帐篷,一个是男生的,一个女生的。会游泳的人,就跳进清澈的水塘里游泳,象我这样不会游泳的人,就在水边钓鱼钓龙虾。其实这并非真正的龙虾,只是一种当地常见的甲壳动物。到了晚上,我们就把龙虾洗干净,用自己带来的锅烧了吃,那种味道胜过了饭店里的海鲜。
第一天的晚上,什么事都没发生。
第二天的晚上,我在帐篷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于是钻了出来。绿色的芦苇深处送出来绿色的风,这股风把我引到了一片芦苇中,我索性脱了鞋子,光着脚走在泥泞里,穿过帏幔般的苇叶,苇尖扫过我的脸颊。我觉得自己变成了隐身,被芦苇荡完全吞没了。我抬起头,看到的天空是在许多随风摇曳的芦苇尖丛中露出的一方小小的深蓝色,水晶般的深蓝,没有一点瑕疵,在这深蓝色的水晶中间是个圆圆的月亮。
我沿着芦苇丛中的一条小河继续走去,拨开密密的苇杆,穿过一个极窄的小河汊,又转了好几个弯,才到了一个被芦苇层层包围起来的更隐蔽的小池塘。我忽然听到了一种奇怪的水声,在月光下,我见到在水里有一个人。
同时,我闻到了一股香味从水中散发出来。
我悄悄地观察着,那是一个女人,只露出头部和光亮的双肩。不知道她是游泳还是洗澡,我尽量克制自己急促的呼吸,隐藏在芦苇丛中。她的长发披散在洁净的水中,舒展着四肢。过了许久,直到我都快站麻了,她才慢慢上岸。我先是看到她赤裸的背脊,两块小巧的肩胛骨支撑起一个奇妙的几何形状。然后,她的腰肢和大腿直至全部身体都象一只剥了壳的新鲜龙虾般一览无遗地暴露在河岸上。她的体形犹如两个连接在一起的纺锤。沾满池水的皮肤被月光照着反射出一种金色的柔光。
我终于看清了她的脸。
——香香。
她虽然只有十八岁,但脸和身体看上去都象是二十出头的女子。
她穿上了衣服,把所有的诱惑都严严实实地包裹了起来。然后她轻轻地说了一句:“出来吧。”
躲在芦苇中的我脸上象烧了起来一样,不知所措地磨蹭了一会儿才慢慢地走出来。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心头砰砰地乱跳,我有些害怕,她也许会告发我,把我当作有什么不良企图。
“对不起,我刚到这里,什么都没看见。”我想辩解,却越来越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
“你看到了。你全都看到了。”香香靠近了我,我的鼻孔里充满了她的气味。
“我不是故意的。”我后退了一步。
“别害怕。”她突然笑了,笑声在夜空里荡漾着,撞到风中摇晃的芦苇上,我似乎能听到某种回音。
“香香,你真的不会告发我?”
“你想到哪里去了,你当然不是故意的。你不是那种人。”香香赤着脚坐在了一块干净的地上,对我说,“来,你也坐下吧。”
我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坐在了她面前,却一言不发。
“你说话啊。”她催促着我。
“我——”我一向拙于言辞的,坐在她面前,鼻子里全是她身上的香味,我差点成了木头人。
“是不是睡不着觉?”
我点了点头。
“我也是。”忽然她对我做了一个禁声的动作,“听。”
四周一片寂静,连风也停了。
“听什么?”我摇了摇头。
“嘘,又来了,听——”
“什么都没听到。”我的听力还可以的啊。
“嗯,现在没有了,那个人过去了。”
“哪个人?谁过去了?”
“你刚才真的没听见吗?是拖鞋的声音,快听——嗒——嗒——嗒,从泥地里走过的声音,我听的很清楚,这么清楚的声音你怎么没听到?”她睁大了眼睛问我,此刻从她嘴里出来的声音让我毛骨竦然。
这时候,风又起来了,芦苇摇晃,我听了香香的话突然有些害怕,我站了起来,向四周张望了片刻,不可能的,不可能出现那种拖鞋的声音,一个人也没有啊。我想去芦苇的深处看看。
“别去。”香香叫住了我,“今天下午我听这里的乡下人说,许多年前,这块池塘淹死过一个来插队落户的女知青,他们说,从此每天晚上,这里的水边都会有拖鞋的声音响起,因为那个女知青是穿着拖鞋淹死的。”
“可我怎么没听到。”但我的心却开始越跳越快。
“乡下人说,一般人是听不到的,而如果有人听到,那么这个人很快就会死的。”她幽幽地说。
“别信那些鬼话。”
“呵呵,我才不会信呢,我是骗你的,不过我真的听到了那种拖鞋的声音。”
“我们回去吧。”我真的有些怕了。
我们绕过那条小河,拨开芦苇,向我们的帐篷走去,突然她停了下来,抬起头看着深蓝色的天空。
“又怎么了?”我问她。
“真美啊。”她还是看着夜空。
“什么真美?”
“流星。我刚才看到了一颗流星,从我的头顶飞过去。”她无限向往地说。
“你运气真好。”我看着天空,心里觉得很遗憾。
回到了营地,我们钻进了各自的帐篷。
那晚,我梦见了一个穿着拖鞋,梳着两根小辫子的女知青。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一钻出帐篷就看到了香香,她向我笑了笑,我也向她笑了笑。
后来,我们分开来自由活动,许多人去了海边,我也去了,回来以后,我们发觉香香不见了,她好象没有去海边。我们到处找她,始终没有找到,一直到了晚上,大家都非常着急,有的人急得哭了,我们向当地人借了煤油灯和手电继续寻找。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地方,于是,我带着大家去了昨天晚上香香游泳的那个小池塘,当我们来到芦苇深处的水边,用手电照亮了水面,在微暗的光线里,我见到水面上漂浮着什么东西。我有了种不祥的预感,我冲到了水边,闻到了一股香味。
漂浮在水面上的是香香。
几个会游泳的男生跳下了池塘,他们把香香捞上了岸。
香香死了。
她平静地躺在岸上,闭着双眼,似乎睡着了,而昨天晚上,她还在这里对我说她听到的声音。我想起了她的那些话,我的眼泪扑簌扑簌地滑落在了地上。当香香被抬走以后,我一个人留在了这里,这里的夜晚静悄悄,我一点都不害怕了,我非常渴望,能够听到那拖鞋的声音的,但是,我什么都没听到。
香香的验尸报告说她是溺水身亡的。可香香的水性是我们这些人里最好的,没有人能够理解。根据规定,香香的遗体必须在当地火化,我们都参加了她的追悼会,在追悼会上,我走过她的玻璃棺材,看着静静地躺在里面的香香的脸,我似乎还能闻到那股香味。
香香,香香,香香。
我想她。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时光倒流,让她再活过来。
我知道这不可能。
每年的清明和冬至,我都会到她的墓前送上一束鲜花。
现在,她的脸又清晰了起来,还有,她的气味,重新使我的鼻子获得了满足。
因为ROSE。
二月十六日
南湖中学位于一大群老房子的中心,从空中俯看就象是一片低矮的灌木中间被某种动物破坏掉了一块,那空白的一块就是中学的操场。
我和叶萧走进这栋五十年代建造的苏联式教学大楼,在空旷高大的走廊中,我们通过这里的校长,来到了档案室。1966年的档案很齐全,但是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用。
老校长喋喋不休地说:“红卫兵之类的内容是不会进入档案和学籍卡的。那一年有几百个学生加入了红卫兵,他们分成了几十批去各个单位‘闹革命’,要想查出哪些人去了南湖路125号简直是大海捞针。”
“那这里还有什么人熟悉当时的情况?”
“这个嘛,过去那些老教师都退休了,现在一时也找不到。恐怕有点难度。”
突然负责档案室的中年女人插了一句话:“校长,教历史的于老师过去不是我们学校66届的毕业生吗?”
“哦,对,我带你们去找他。”
校长带着我们走出档案室,在一间办公室里,校长对着一个正埋头看书的中年男子说:“老于,你不是我们学校66届的毕业生吗,市公安局的同志想调查一下66年我们学校红卫兵的一些情况。”
于老师抬起了头,他的神色突然变得紧张起来,他看了看我们,然后表情又平和了下来,淡淡地说:“校长,三十多年前的事,我都记不清了。”
校长对我们摇了摇头,轻轻地对我说:“你们别介意,他平时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性格内向,不太喜欢和别人说话。”
叶萧向我示意地点了点头,然后说:“于老师,能不能耽误你一点时间,我们到外面去谈谈。”
“我正在备课呢。”他有些不耐烦了。
“对不起,我正在办案。”叶萧直视着他的眼睛。
他们对视了一会儿,最后,于老师的目光避开了他:“好的,我们出去谈吧。”接着他又对校长说:“校长,你回去忙吧,我会配合的。”
穿过阴暗的走廊里,我们来到了操场边上,阳光懒洋洋地照着我的脸,一群上体育课的学生正在自由活动。叶萧抢先开口了:“于老师,1966年你是红卫兵吗?”
“是,但这重要吗?当时几乎每个学生都是。”
“对不起,你也许误解我们了,我们只是来调查一些事的。你知道南湖路125号这个地方吗?”
“黑房子?”他突然轻声地,几乎是自言自语地冒出来一句。
“什么是黑房子?”我问他。
他不回答,长长地叹出了一口气,然后看了看四周,把我们带到操场最安静的角落里,那里种着几棵大水衫,还有一些无花果树,地上长满了野草。在树荫下,阳光象星点一样洒在我们的额头,他缓缓地说:“因为那里是一栋黑色的楼房,十分特别,我小时候就住在那儿附近,所以我们那时候都把那地方叫做黑房子。”
“我们就是为了这栋房子而来的,于老师,我想你一定知道些什么,把你知道的全告诉我们,要全部。”叶萧说。
“1966年的秋天,我是这所学校里毕业班的学生,我们绝大部分同学都成为了红卫兵,批斗老师,搞大字报大辩论,但是许多人感到在学校里闹还不过瘾,于是有一群红卫兵去了黑房子。而我,也是其中的一员。”他突然停顿了,在我们目光的催促下,他才重新说起来,“你们年轻人不会理解当时的情况的,每个人都象疯了一样,尤其是十六七岁的学生,有许多事,需要时间才能让我们明白。我们去黑房子,因为那里是一个有许多知识分子的事业单位,据说是什么走资派的大本营。我们进去把里面的工作人员都给赶了出来,没人敢反抗,我们在所有的房间里都写上了大字报。最后,只剩下了地下室。我们命令看门的打开地下室,然后我们下去,那个地下室非常深,我们走台阶走了很久,回想起来挺吓人的,但是少年人有着强烈的好奇心,红卫兵又号称天不怕地不怕,终于,我们壮着胆子下到了地下室里。我们发现了一个玻璃棺材,在玻璃棺材里,躺着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
我倒吸了一口冷气,果然,1945年以后,皇后的遗体留在了地下室里。我再看了看于老师的脸,他的双眉紧锁在了一起,低下了头。
“继续说吧。”
“当时我们非常惊讶,一方面因为我们还小,不懂女人,一下子看到一个如此美丽的女人一丝不挂躺在玻璃棺材里,与其说是害怕,不如说是惊喜。是的,她太美了,我一生都没有见过那么漂亮的女人,大约20岁出头的样子吧,浑身雪白,闭着眼睛,安详地睡着。
一开始我们还真的以为她是在睡觉,我们有些害羞,想躲出去,后来有人说,一个女人脱光了衣服睡在这里肯定是个女流氓,要对她实施无产阶级专政。于是,我们打开了玻璃棺材,叫她起来,但是她却没有反应,我们中的一个人大着胆子碰了碰她,却发觉她的身上是冷的,再摸了摸脉搏,才知道原来她已经死了。一下子我们变得害怕起来,我们开始猜测她会不会是被人谋杀的,但实在也想不出什么结果,我们不敢把这件事说出去,因为我们看见了裸体的女人,也许会被别人认为我们也是流氓。我们只能例行公事一般在墙上涮上了大字报的标语,然后离开了地下室。”
“就这么简单?”我怀疑他还藏了些什么。
“不,当时我们白天在黑房子里闹所谓的革命,晚上还照样回家睡觉,毕竟我们还是孩子。进入地下室以后的第二天早上,我们象往常一样在黑房子门口集合,但是发觉少了一个人,叫刘卫忠,于是我们到他家去找他。到了他家里才知道,刘卫忠昨天晚上喝了一瓶老鼠药自杀身亡了。而昨天,只有他摸过地下室里的女人。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感到非常害怕,我离开了他们跑回到家里,再也不敢去黑房子了,那天我在家里窝了一整天,提心吊胆的。到了晚上,十点多了,我已经睡下了,突然张红军到我家里来了,他也是红卫兵,昨天也和我们一块去过地下室。他说他很害怕,晚上做恶梦睡不着觉,所以来找我,他告诉我一件事:昨天晚上,他和刘卫忠两个人偷偷地去过黑房子,他们发觉看门的人已经逃走了,大门开着,于是他们进去下到了地下室里。张红军说,他去地下室只是想摸摸那个女人,因为刘卫忠说这种感觉很舒服,他是在刘卫忠的鼓动下才去的,他说在地下室里,他们摸了那个女人的身体。”
“只是摸吗?”叶萧突然打断了他的话。
“我知道你想到了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就喜欢胡思乱想,那时候的我们很单纯,能摸一摸女人就已经被认为是大逆不道了。”
“对不起,请继续说。”
“那晚张红军说,他没想到刘卫忠会自杀,一点预兆都没有。我问他这件事情还告诉过谁,他起初不肯说,后来才告诉我,下午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件事说给那些去过地下室的红卫兵听了。后来实在太晚了,那时候的人们睡的都很早,张红军被我父亲赶走了。
第二天,我还是没有去黑房子,我对那里产生了深深的恐惧,我去了学校,清晨的校园里没有一个人来上课,我在操场里转了转想呼吸新鲜空气。但是,我在操场上发现了张红军,对,就在这里,就是现在我们站着的地方。他就躺在我们脚下的这块地方,口吐白沫,手里拿着一瓶农药。”他痛苦地低下了头,看着这片杂草丛生的地面,“当时的验尸报告说他是在那天凌晨三点钟左右喝农药自杀的。也许我永远都无法理解他和刘卫忠自杀的原因。”
我的脚下忽然生起一股冰凉的感觉,我急忙后退了几步,我真没想到,1966年,我鞋子底下的这块地方居然死过人。
“那么其他人呢?”叶萧继续问。
“以后他们的事我就不知道了,张红军死了以后,我再也没有参加红卫兵的任何活动了,不久以后,我就离开了上海,去云南上山下乡了。后来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以后,我考上了大学,毕业后成为了一名教师,被分配到了我的母校教书,一直到现在。”
“就这些吗?”
“我知道的全是这些了,那么多年来,我每次要路过黑房子的时候,总是绕道而行,尽量不看到它,那是一场恶梦,我一直生活在这阴影中。”从他痛苦的脸,我可以看出他的确没说谎。
“谢谢。能不能告诉我当时去过地下室的其他人的名字。”
“还好我一直记得他们。”他拿出纸和笔,写下了十几个名字,然后把纸交给了叶萧。
“非常好,谢谢你的配合,再见。”我们刚要走,于老师突然叫住了我们:“对不起,我想知道,你们去过那个地下室吗?”
“去过。”
“那个女人还在吗?应该已经成为一堆枯骨了。”于老师说。
“不,她已经不在了,但是,她不会变成枯骨,她永远是她。”我回答了一句。
我能看到他惊恐的眼神。
二月十七日
我又梦见了香香。
我实在在家里呆不住,我出去了,天色已晚,我在上海的街头游荡着。不知逛了多远,我突然看到眼前矗立着那尊有名的普希金雕像。看到沉思的诗人,我知道我该去哪儿了,又穿过两条马路,我拐进那条小巷,走进小楼,在三楼的一扇门前停了下来。
但愿ROSE在家。
天哪,黄韵的脸又浮现了,我承认我是个容易遗忘过去的,和所有的男子一样喜新厌旧的人,但是,我永远无法遗忘的是香香。
我敲了敲门。门开了,是ROSE。她很吃惊,然后对我笑了起来。她的房间还是我上次见到的老样子。只是电脑开着,一个系统软件的界面。
“请坐啊,你怎么会来?”她坐在一张摇椅上。
“顺便路过而已。”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路过。
“你撒谎。呵呵,你一撒谎就会脸红。”她轻轻的笑声塞满了我的耳朵,还有那股熟悉的香味。
我摸摸自己的脸,挺热的,的确是红了,我想转移话题,把目光盯着电脑问:“你在玩什么呢?”
“我在编一个程序,我被那家网络公司录取了。”
“恭喜你了。”
“没什么啦,就是编辑一些防范黑客和病毒的软件而已。”
我又没话了,好不容易才想出一句:“谢谢你上次送我回家。”
“我可不想让你在仙踪林茶坊里过夜。那天你到底睡着了没有?”
“没有,回到家以后才睡着的。”
“哦,那你还知道啊,别看你人瘦,扶着你还挺吃力的。”
“真不好意思,我怎么会那么狼狈呢,你可别以为我有什么病啊,我挺健康的,过去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真搞不懂。ROSE,为什么我看你摇来摇去,就有一种摆钟摇晃,时间停顿的感觉,然后我的眼皮就跟着你动了起来。”
ROSE把双手向我一摊:“我可不知道。”
“你能不能再试试?”
“随便你。”她坐在她的摇椅上晃了起来,就和上次在仙踪林里一样。一前一后,她的脸离我一近一远,从清晰到模糊,再从模糊到清晰,甚至连她的那股天生的香味,也随着她的摇动而一浓一淡。我的眼皮再次被她控制,我的视线从明亮到昏暗,再从昏暗到明亮,在明亮和昏暗的中间,是她的眼睛。
但我的意志是清晰的。
是时候了,我必须要说出口,这两个字在我心里酝酿了酗酒,终于,两眼无神的我对ROSE轻轻地说:“香香,香香,香香。”
ROSE的眼睛明亮了些,我能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一些别的东西,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我听到了她的回答:“听——”
我半梦半醒地回答:“听什么?”
“嘘,又来了,听——”
“我只听到你的声音。”房间里没有任何其他的声音,我的视线有些糊涂,但我的耳朵还完全正常。
“嗯,现在没有了,那个人过去了。”
“哪个人?谁过去了?”
“你刚才真的没听见吗?是拖鞋的声音,快听——嗒——嗒——嗒,从泥地里走过的声音,我听的很清楚的,这么清楚的声音你怎么没听到?”
天哪,这些几句话怎么这么熟悉,在我的记忆深处锁了许多年了,那些痛苦的回忆。没错,那是香香说过的话,那天晚上,在池塘边上,芦苇荡里,在她死的前一夜。
怎么从ROSE的嘴里说出来了?
她继续说:“今天下午我听这里的乡下人说,许多年前,这块池塘淹死过一个来插队落户的女知青,他们说,从此每天晚上,这里的水边都会有拖鞋的声音响起,因为那个女知青是穿着拖鞋淹死的。”
怎么回事,难道时光真的倒流了?难道这里不是ROSE的家,而是在十八岁时的苏北芦苇荡中的一个夜晚。
她还在继续,声音越来越低缓:“乡下人说,一般人是听不到的,而如果有人听到,那么这个人很快就会死的。”
我静静地听着,我的眼皮一闭一合,但我的耳朵听得清清楚楚,绝不会听错。我快疯了。我知道,还有一句话——
“呵呵,我才不会信呢,我是骗你的,不过我真的听到了那种拖鞋的声音。”ROSE把这最后一句话说了出来。
然后,她停止了摇晃。
我的眼皮恢复了正常,我睁大着眼睛,看着她,没错,她是香香。她就是香香。她的眼睛,她的脸,她的香味,她说的话,每一样,她都是香香。
“ROSE,你到底叫什么名字。”我靠近了她,双眼直逼着她。
她呡了呡嘴唇,幽幽地说:“我叫香香。”
“请再说一遍。”我有些痛苦。
“香香,我叫香香。”
我在发抖,我不知道我应该高兴还是害怕,我只知道,香香已经死了,我亲眼看到过她的遗体,她确确实实地已经死了,已经在那个苏北小镇上火化了,我理解不了,我痛苦地说:“这不可能。”
“世界上没有不可能的事。”她靠近了我,她的香味刺激着我,“我回来了,我从那个池塘里游了出来,我上了岸,我自己回了家,我考上了大学,我大学又毕了业,我工作了,我又遇见了你——我所爱的人。”
听到了她的最后一句话,我所有的防线都崩溃了,我的内心决堤了,是的,我承认,她是香香,她绝对是香香,没人能冒充的了。我的香香,我的香香又活了回来,我的香香没有死,她没有死。香香就是ROSE,ROSE就是香香。
我开始相信了她的话,生命是可以永存的。
我相信了复活。
我相信了时间的黑洞。
现在,我的香香就在我的面前,她靠近了我,她和我在一起,没有别人,我忍耐了那么久,因为我有一个强烈的冲动,我要得到她。过去我以为我永远都得不到她了,现在我知道我错了,我还可以得到她,拥有她,就是现在。
让这个世界崩溃吧,只有我,和她。
香香,我来了。
这一晚,我和她,完成了我们应该完成的一切。
她很快乐。
一切结束以后,在幽暗柔和的灯光下,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当我的目光触及她光滑的腹部的时候,我看到了一道淡淡的伤痕,淡红色的,象是一条直线似地镶嵌在白色的皮肤上。
我把头垫在她柔软的腹部,闻着那股香味,象个刚出生的孩子一样睡着了。
我睡得很熟,很熟。
二月十八日
我的耳朵里听到了鸟叫,各种各样的鸟,我醒了,我知道清晨到了。我睁开眼睛,看到了蓝蓝的天空。
多美的天空啊。
我感到了有点不对劲,怎么早晨睁开眼睛,看到的不是天花板而是天空。我支起了上半身,我看到自己正躺在一张绿色的长椅上,我的四周是树林,眼前是一条林间小径。我穿着衣服,衣服外面还盖着一条毛毯,我发觉自己身上有些湿,我用手一摸,全是清晨的露水。
“香香。”我喊了一声。没人回答,只有鸟儿在叫。
怎么回事?我站起来,看着周围的一切,一个人影都没有,我再看了看表,才早上六点半。
我想起了昨晚发生的事,我去了ROSE的家里,她承认她就是我的香香,我得到了她。然后,我头枕着香香的身体睡着了。
这一切是真实的,不是我的幻想,而是确确实实发生过的事,就在昨晚。
可是,现在又是怎么回事,我应该躺在香香的床上,看着她,看着她家的天花板和窗户。而此刻,当我醒来,却发现自己独自一人盖着条毛毯躺在小树林里的长椅上,就象个流浪汉。
我要去找香香。
我抓起毛毯,离开了这片小树林,穿过林间小径,惊起了几只飞鸟,它们扑扇着翅膀,发出羽毛的声响飞向天空。清晨的林间笼罩着一层薄雾,我踏着露水走上了一条更宽阔些的石子路。这里还有一个池塘,有些红色的鱼正在水里游着,我通过一座跨越池塘的木桥,看到了一堵围墙。透过围墙,我能看到墙外面的几栋高层建筑。还好,我现在至少可以确定自己不是在荒郊野外了。
沿着围墙,我见到了一扇门,门关着,我打不开,我明白,这里应该是一个市区的小公园。我在一片树丛里等了一个多小时,公园终于开门了,我从大门里走了出去,公园卖票的人显然大吃一惊,他来不及叫我停下来,我已经走到马路上了。
我看了看路牌,这里应该是徐汇区,离香香的家不远。
我来到了昨晚我来过的地方,宽阔的巷子,一栋小楼的三层,我敲了门。
没人开门。
再敲,我敲了很久,整栋小楼都可以听到我急促有力的敲门声。也许她出去了?
忽然隔壁另外一扇门打开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走了出来。
“别敲了,你是来租房子的吧。”老太婆说。
“不是,我是来找人的。”
“你是说那个小姑娘啊,她今天早上已经搬走了。”
“这怎么可能,昨天晚上——”后面那句“我还在这里过夜”的话我没敢说出来。
“搬走了就是搬走了,今天早上八点,搬场公司来搬走的,她还给我结清了房租。你不信我开门给你看看。”说着,老太婆从掏出了一串钥匙打开了门。
我冲了进去,房间里空空荡荡的,什么都没留下,房间里只剩下一股淡淡的香味,没错,我不会记错的,我还记得这里墙壁和天花板,就是这里。
她为什么搬走呢?
“阿婆,请问你知不知她搬到哪里去了。”
“我哪里知道。”老太婆不耐烦地回答。
“那么她是什么时候租这房子的?”
“去年九月吧。”
“那她在这里租房子是不是该到派出所去登记的?”我知道这个可能性不大,尽管的确有这样的规定。
“喂,你什么意思啊,你是来查户口的啊,去去去,”老太婆把我向外推了一把,接着嘴里嘟嘟囔囔地:“小赤佬,不正经。”
我知道在这里是问不出什么了,我走出了这栋小楼,再回头望望那个小阳台,我突然感到了自己的无助。
香香,你在哪里?
二月十九日
今天我的脑子里全是香香。
我坐卧不安,细细思量着前天晚上和昨天早上发生的一切,但我却丝毫无法理解香香为什么要这么做。她就象一个谜,突然地解开谜底,又突然地变成另一个谜。
我打开了电脑,上网。我先去了我常去的一家国内的大型综合网站,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闻,无非是些东剪西贴来的东西。当我要从首页退出时,我忽然发现左下角的友情链接里,发现了四个楷书字“古墓幽魂”。
不会搞错吧,怎么这里会有“古墓幽魂”的链接,要知道这家大型网站每天的浏览量有几百万,它的链接通常都是同样重要的著名网站,而古墓幽魂最多只能算是个人主页。会不会是其他同名的网站?我点了点链接地址,没错,的确是我所去过的那个古墓幽魂。
不行,我必须阻止他们,古墓幽魂放在著名网站的首页链结里,肯定会引来许多网友去登陆,也许会有更多的人遭遇不测。我立刻给该网站发了封MAIL,希望他们立刻停止链结古墓幽魂。
接着,我上了另一家国内的著名网站,令我吃惊的是,这家著名网站的首页里也有古墓幽魂的链接。接着我又换了一家国内大型网站,居然还是跟前面的一样。
忽然,我在这家网站的新闻里看到了一则报道——“神秘病毒袭击各大网站,首页链结遭到篡改”,我打开这则新闻读了读内容——“据国内各大网站的消息:日前,国内各大综合性门户网站,均遭到神秘病毒的攻击,所有被攻击的网站的首页链结的内容均被篡改,出现了一个叫古墓幽魂的链结站点。
据专业人士称,该网站系本市的一家个人主页,主题为中国的古墓,目前已经请求公安机关介入此事,具体详情不明,但至少可以确知的是,该病毒系通过黑客入侵者的方式传播,虽然被入侵的网站有严密的防范黑客系统,但是,入侵者具有更为高超的技术手段,轻而易举地修改了各网站的内部系统。各大网站的技术人员正在加紧努力修复被篡改的首页,但是目前为止,尚无法成功。但请网友不必担心,被篡改的仅为首页链结,不会影响到其他内容,网友的个人资料也未被黑客盗取。”
遭了,我早就料到古墓幽魂有某种极为高超的技术手段,但没想到它开始用病毒攻击各大网站了,通过这种方式,它可以使它的浏览量大幅度上升,简直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
当我胡思乱想的时候,门铃响了。
是叶萧。
从第一眼我就可以看出,今天的他的情绪似乎特别糟糕,他一进来,我就把网上的发生病毒事件告诉了他。他平静地点了点头说:“我已经知道了,前几天就发生了,我们动用了一切先进的技术手段,始终没能查出谁是古墓幽魂的策划者。我还尝试过删除其内容,也失败了,虽然地址应该就在本市,但是我们根本无法靠近它,怎么也找不到,就象是一个幻影。”
“的确象幻影,你曾经说过,那些不明不白的自杀者就象中了某种会传染的病毒。现在来看真的是病毒。”我担忧地说。
“是的,现在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似乎这些日子来,古墓幽魂的技术水平在不断提高,现在古墓幽魂可以通过病毒来篡改首页链结,将来就可以直接篡改各大网站的网页内容,到那时候,就会非常可怕了。”
我的脑子里瞬间浮现出一副图象,在一家国内著名网站的网页里,突然变成了黑色的屏幕,出现了一个骷髅,一个墓碑,还有清朝皇帝的画像,然后冒出一行字——“她在地宫里”。所有的网民都象那些自杀者一样沉迷于其中,最后全都——我想象不下去了。
真的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想些别的吧,我问叶萧:“你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些?”
“当然不是,上次我们在南湖中学,那个于老师给了我们一个1966年去过地下室的红卫兵的名单。我今天去户政档案部门查过这些名单上的人了。我复印了一份资料给你看看。”说着,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了一张纸递给了我。
“刘卫忠,男,生于1950年3月17日,1966年10月15日晚在家中服鼠药自杀身亡。”
“张红军,男,生于1950年1月26日,1966年10月17日凌晨在南湖中学操场服农药自杀身亡。”
“穆建国,男,生于1949年11月6日,1966年10月18日晚在南湖路上故意冲向疾驶的卡车身亡。”
“吴英雄,男,生于1950年5月15日,1966年10月19日凌晨在家中上吊自杀身亡。”
“张南举,男,生于1949年9月27日,1966年10月19日凌晨跳入苏州河自杀溺水身亡。”
“辛雄,男,生于1950年2月10日,1966年10月19日晚在家中服毒自杀身亡。”
“冯抗美,男,生于1950年6月18日,1966年10月20日凌晨在其父单位内割腕自杀身亡。”
“樊德,男,生于1949年12月2日,1966年10月23日晚在家中上吊自杀身亡。
“成叙安,男,生于1950年4月18日,1966年10月23日晚在南湖路上割腕自杀身亡。
“罗康明,男,生于1949年11月27日,1966年10月24日凌晨在一栋南湖路125号大楼上跳楼自杀身亡。”
“陈溪龙,男,生于1949年10月12日,1966年10月24日凌晨在家中上吊自杀身亡。”
“李红旗,男,生于1950年1月15日,1966年10月下旬失踪。”
“黄东海,男,生于1950年3月21日,1966年10月下旬失踪。”
看完了之后,我感到毛骨竦然,从1966年10月15日到10月24日,短短的九天的时间内,包括于老师说过的两个人在内,总共有十一个人自杀身亡,另有两人失踪,他们都去过地下室见过皇后,除了于老师没有继续去过那里以外,其他人都遭遇了不测。
叶萧缓缓地说:“你仔细地看,其中有两个死亡高峰,即从10月18日晚到10月20日凌晨,共死了五个人,10月21日和10月22日都没有死人,但是从10月
23日晚上到10月24日凌晨,其实只有一晚的时间,就又死了四个人。至于那失踪的两个人,我估计恐怕是死了以后没有找到尸体才被定性为失踪的。”
“这样说,所有的线索都断了?”
“差不多吧。”叶萧苦笑着说,“我决定放弃了。”
“你说什么?”
“放弃,我厌倦了,我厌倦了这一切,我不想再继续了。”他低下了头。
“我们努力了那么多,从古墓幽魂到东陵,到发现皇后的事情,再到现在,难道我们的努力都白费了。”
他不回答,沉默了许久,我也不说话,我的房间里死一般寂静。忽然他说话了,声音非常轻,低沉地吐出几个字:“我很害怕。”
“公安局的也会害怕?”我很奇怪。
“够了,我也是人,我真的很害怕,从一开始,我知道这案子,看到那些死者的资料,进入古墓幽魂的网站,去东陵,调查那些档案和资料,这些事情,每一分钟,我都是在极度恐惧中度过的。你不会理解的,我总是在表面上装出一付胸有成竹的样子,其实,我的心理比你还脆弱。”
“我要依靠你。”
“听着,每个人都有权利害怕。”他抬起头看着我,一字一顿地说着,他睁大着眼睛,额头冒着汗,那一副表情我从来没见过,我心中突然有些隐隐的恐惧,他会不会也——
叶萧继续说:“现在,我心理最后的防线终于崩溃了,我已经失去任何希望了,我想活下去,活下去,从一开始,我所谓的调查就是我的自作主张,现在是该退出的时候了。”
“你真的变了很多,我记得过去我们小的时候,你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害怕。”
“是的,我变了许多。你一定要知道原因吗?”
“如果你愿意告诉我的话。”
“那是恶梦,我不敢回忆的恶梦。我在北京读公安大学的时候,我谈过一个女朋友,是我的大学同学。我们谈得很好,在一起很开心,后来,我们毕业以前,去云南实习,跟着云南的一个缉毒队,我和我的女朋友也在一起,在一次缉毒行动中,不幸出现了意外,贩毒分子的力量要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我的女朋友被他们扣留了。
几天以后,我发现了我的女朋友的尸首。简直惨不忍睹,她被他们轮奸了,浑身上下到处都是被注射的针孔,他们给她注射了大量的海洛英,她是在极度的痛苦中死去的。当时在现场我逮捕了其中的一个毒贩,我把他拷了起来,用枪指着他的脑袋,我的女朋友的尸首就躺在我身边,我非常愤怒,我恨那些家伙,恨到了极点,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报仇,为她报仇。我差点就扳动扳机了,子弹将从枪口射出,把那个混蛋的脑浆给打出来,但是,在抠动扳机前的一瞬,我想到了——如果我开枪,那么我就违反了纪律,甚至违反了法律,因为他已经被抓住了,没有反抗,我不能打死他。
那个瞬间,我更加痛苦,我在报仇与执行公务间选择着,我真的非常想看到那家伙脑浆迸裂的样子,因为我的女朋友,我所深深爱着的人死得太惨了。最后,我没有开枪,我放下了枪,把他押回了警局。
后来,我总是给自己找许多理由,总是自我安慰说自己遵纪守法,其实我知道这些全是假的,我是因为害怕,我害怕,我害怕看到杀人,我害怕我被开除出公安,尽管我有报仇的冲动,但这种强烈的冲动在我的害怕面前居然一点作用都没有了。我害怕,真的害怕,也许在骨子里,我真的是一个胆小鬼。
所以,后来我没有参加刑警,而是在信息中心搞电脑,我再也没有碰过枪。就是这样,我变了,我发现了我心底深埋着的那种东西,那是害怕,是恐惧,天生的恐惧。而自从,发生了最近的这些怪事以来,我的恐惧就与日俱增了,我觉得那种害怕每夜都纠缠着我,我现在几乎每晚都要梦见我的女朋友死时的景象,我受不了。就这么简单。”
他哭了。从小到大,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眼泪。
“叶萧,对不起,我不该让你把这些痛苦的事情都说出来。”我想安慰他。
“好了,说出来就没事了。”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擦了擦眼泪,然后摇了摇头,站了起来,“我走了,我要回去早点睡觉,记住,别再管这件事了,我不想失去你,兄弟。”他抱住了我的肩膀,我们就象亲兄弟一样,我觉得我重新找回了小时候的那种感觉。
我送他出门,嘱咐他路上当心,然后我回到了房间里。
害怕。
什么是害怕,是恐惧吗?
我看了看那天ROSE(香香)送给我的白玫瑰。
玫瑰已经枯萎了。
二月二十日
我又上网了,几乎每个我上过的综合网站的首页里都能看到古墓幽魂的链结,一看到这四个字我就一点兴趣都没有了。于是,我一头钻进了我喜欢的一个论坛。
我发现今天几乎每一个贴子都只有五个字——“她在地宫里”。发贴人叫“古墓幽魂”。古墓幽魂在灌水?还是有人的恶作剧。我立刻发了一个贴子:“请版主删除所有的灌水贴子”。发完了以后,不可思议的是,我发现我的新贴子居然变成了“她在地宫里”,我的ID也变成了古墓幽魂。一定是服务器有问题,遭受病毒攻击了。
我该怎么办。
我关了电脑,静静地想了一个多小时,我想到了许多,想到了这两个月来所发生的这些匪疑所思的事情,还有那些死去的人,我看了看窗外,黑沉沉的夜色,就象冬至前夜的那晚,所有恶梦的开始。
也许还会有更多的人死去。
必须要阻止它。
我终于上了古墓幽魂。
首页还是老样子,不同的是浏览量发生了巨大变化——“您是第1072982名访问者”;“在线人数3197人”。我吓了一大跳,访问量居然超过一百万人次了,而上一次还是几万,看来古墓幽魂对各大网站的病毒攻击获得了显著的效果。
接着,我进入留言版,铺天盖地的贴子,我看了一会儿,全是些新来的人发的贴子,他们似乎都很兴奋,非常喜欢这里,许多人讨论如何玩最后那个迷宫游戏。然后我刷新了以下,又多出了十几条贴子,我再看了看点击数,一个一小时前的贴子,点击数已经超过了一百。真难以置信。
我再进入聊天室,还是一样,密密麻麻的名字,至少有一百多个,拉得我手都酸了。我不敢和他们对话了,我离开这里,进入了明清古墓中的清东陵。再进入惠陵,还是那五个字——“她在地宫里”。
进入迷宫。
系统还保留着我上次到达的地方,我继续前进。还是黑色的地道,前面一束微光,上下左右全是黑色石头砌成的,还有自己的脚步声。一个又一个分岔路口,我几次迎头“撞”上黑色的墙壁,音箱里传来非常逼真的“砰”的一声。我几乎能感觉到自己的额头产生了一种剧痛。我想到了这些天来我所看的那些资料,还有南湖路黑房子里那个地下室。
我的脑子里全是“地宫”这两个字,没错,现在电脑屏幕里的环境就是地宫,那天我下到地下室里时产生的恐惧与我现在的感觉是相同的。也许我真的离她越来越近了,我加快了速度,我觉得我越来越熟练了,我能非常有预见性地避开那些死胡同,如果我选择错了岔路,我就会七拐八弯地进入一个最终是没有出路的地道,然后我要再费很大的力气退回来。左面笼罩在地形图上的黑雾正在一步一步退去,一个小时以后,几乎已退去一半了。
忽然,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一个人影,那个人影越来越近,直到来到我面前,拦住了我的去路。难道又是叶萧?
我在下面的对话框里面打了几个字:你是叶萧吗?
接着对话框里的回答让我吃惊——
香香:我是香香。
我:香香,怎么是你,你怎么在这里,快离开,马上就离开。
香香:不,该离开的是你。
我:我不会走的,香香,你为什么离开了我。
香香:对不起,我有我自己的原因。
我:告诉我什么原因。
香香:你不能知道。
我:我想见你。
香香:现在见吧。
电脑屏幕里我面前的那个人逐渐地清晰了起来,黑色的雾气消失了,我看到了那个人的脸——香香。
音箱忽然响了,传出了香香的声音:“离开我,永远离开我。”
我继续在对话框里打字:不,我一定要找到你,无论你在天涯海角。
音箱沉默了片刻,接着又响了:“你不后悔?”
我:绝不后悔。
接着,电脑屏幕里香香的脸靠近了我,越来越近,直到整个屏幕都是她的脸,屏幕的中心是她红色的嘴唇,她的嘴唇有些变形了,就象是把嘴唇贴在了摄像机镜头上,我明白了,她在吻我,我能感觉到她嘴唇上的温度。
我也在电脑屏幕上吻了她的嘴唇。
瞬间,她的嘴唇消失了,她整个人也消失了,前方的地道里空空荡荡。
刚才也许是吻别。
我不后悔,我要找到她,我继续前进。我越来越感受到了地宫与墓室里的气氛,我知道那扇大门已经为我开启了,地形图里一大半的空间已经显露出来了,在地宫的中心,我知道,她在那儿。
我来了。
我终于闯进了地宫的中心。
那是一个巨大的空间,黑色的雾气笼罩着四周,头顶是黑色,脚下是黑色,前后左右都是黑色,在这黑色世界的中心,有两口硕大的黑色棺椁。
我点击了其中较大的一个棺材,棺盖打开了,我看到里面是一具穿着清朝皇帝龙袍的白色骷髅。
我知道,他是同治皇帝。
那么下一个呢?
我会看到什么?
我的鼠标移动到了第二个棺椁上面,停留了片刻,我的手指似乎不听我自己指挥了,僵硬了一会儿,终于,我深呼吸了一口,连着按了两记左键。
棺材盖打开了。
屏幕变成了一片黑色,在黑色的中心,出现了一只眼睛。
确切地说,是一个女人的眼睛。
我能到这只眼睛有长长的睫毛,乌黑的眼球,明亮的眸子,黑洞般的瞳孔。我又产生了那种感觉——这瞳孔象个无底洞,象个深深的水井。
灯灭了。
一瞬间,我房间里的灯灭了,全部的灯,包括电视机的电源灯也灭了,整个房间里一片漆黑。怎么回事,也许停电了?天哪,但愿只是停电而已。但我却感到了一种心底自发的恐惧,深深地渗透进了我全身每一寸皮肤,黑暗是恐惧的根源,陷入黑暗中,每个人心中,都会把自己深埋着的恐惧挖掘出来。我不想挖掘这恐惧的潜力,但我无法抗拒,我无能为力。但我又无法确知这恐惧到底在哪里,但我突然产生了一种直觉——恐惧就在我背后。
电脑屏幕里的那只眼睛消失了,而变成了一片灰色。
十几秒钟以后,灰色的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行字——看看你的身后。
我回过头去。
一个人影,我看到一个人影站在我的背后。
我把手放在了自己的胸口上,我能感到自己的心跳几乎要穿出自己胸膛了。我站了起来,借助着电脑屏幕里发出的微弱的灰色的光线,看着我身后的人影。
人影向前移动了一步,不是我的幻想,而是确确实实存在着的一个影子,而且是女人的影子,就在我的房间里,就在我的面前。
电脑屏幕灰色的光线照射在那个人的身上。
香香。
她全身穿着白色的衣服,脸色苍白,面无表情,我能感到她的身上发出一种寒冷的气息。
“香香。”我叫她。
她不回答,只盯着我看,几秒钟后,从她的嘴里,一字一顿地吐出几个字:“还——我——头——来——”
那不是她的声音,我确信,这绝对不是她的声音,无论是十八岁时候的香香,还是我的ROSE,都不是这个声音,而是另外一个女子的声音。这声音充满了哀怨,充满了仇恨,不象是从我的房间里的人发出来的,而是从地下发出的声音,就象是把自己的耳朵贴在地面上而听到的那种声音一样,异常地沉闷。
当她说完这四个字,突然,我房间里的灯全都亮了。
在这瞬间,她消失了。
我的眼睛刚从前面的黑暗中出来,还没恢复,我使劲地揉了揉眼睛,再看了看我的房间,她不见了,的的确确消失了,就象这空气,这光线一样。
我再看了看电脑,我的电脑居然已经自动关机了。
我长出了一口气,又坐了下来,我的额头上全是汗,我知道我刚才恐惧极了。我不敢再回想刚才发生的事情了。我匆忙地睡下了。
我梦见了一个女人。她有丰满的胸脯,修长的手臂和腿,白皙光滑的皮肤,惟独缺了一样——她的头。
一个没有头颅的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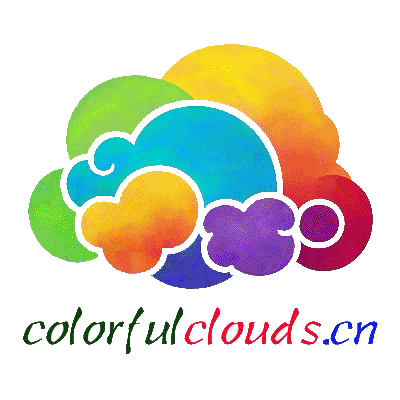
|
当我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发觉自己穿着外衣躺在被子里,手里还攥着一束白色的玫瑰花,样子有些滑稽,我起来洗了一个澡,才渐渐地清醒了回来。
我家里没有花瓶,我只能把玫瑰花插在平时放牙涮的茶杯里,倒有了些后现代的味道。
我仔细地回忆着昨晚每一个细节,想着ROSE的脸,还有她身上的那股气味,那股气味刺激了我的嗅觉器官,使我开始用自己的鼻子回忆起了另一个女孩。
香香。
我叫她香香。
ROSE的脸,长得和她一模一样。
从我第一眼见到ROSE起,我就又想起了香香,想起了她的脸,她的气味。
我叫她香香,因为她天生就有香味,从她的身体里散发出来的香味。
我能用自己的鼻子在一万个人中分辨出香香来,我发誓。
但这再也不可能了,因为,香香已经死了。
她死的时候,只有十八岁。
我想她。
在那个夏天,炎热干燥的夏天,副热带高气压控制着我们的城市,连坐在家里都会出一身大汗。香香是我的同学,我们班级还有其他十几个人,除了林树以外,我们全都报名参加了一个三日游的野营,去了江苏的一个海边小镇,据说那里非常凉爽。
坐了五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和轮渡,我们达到了一片广阔无边的芦苇荡。那儿有大片的水塘和泥沼,长满了比人还高得多的青色芦苇,范围有上千亩大。一旦你躲在其中某个地方,密密麻麻的芦苇足够把你隐藏,谁都无法找到你。我们就在芦苇荡中间的一片干燥的空地里扎下了营,搭起了两个大帐篷,一个是男生的,一个女生的。会游泳的人,就跳进清澈的水塘里游泳,象我这样不会游泳的人,就在水边钓鱼钓龙虾。其实这并非真正的龙虾,只是一种当地常见的甲壳动物。到了晚上,我们就把龙虾洗干净,用自己带来的锅烧了吃,那种味道胜过了饭店里的海鲜。
第一天的晚上,什么事都没发生。
第二天的晚上,我在帐篷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于是钻了出来。绿色的芦苇深处送出来绿色的风,这股风把我引到了一片芦苇中,我索性脱了鞋子,光着脚走在泥泞里,穿过帏幔般的苇叶,苇尖扫过我的脸颊。我觉得自己变成了隐身,被芦苇荡完全吞没了。我抬起头,看到的天空是在许多随风摇曳的芦苇尖丛中露出的一方小小的深蓝色,水晶般的深蓝,没有一点瑕疵,在这深蓝色的水晶中间是个圆圆的月亮。
我沿着芦苇丛中的一条小河继续走去,拨开密密的苇杆,穿过一个极窄的小河汊,又转了好几个弯,才到了一个被芦苇层层包围起来的更隐蔽的小池塘。我忽然听到了一种奇怪的水声,在月光下,我见到在水里有一个人。
同时,我闻到了一股香味从水中散发出来。
我悄悄地观察着,那是一个女人,只露出头部和光亮的双肩。不知道她是游泳还是洗澡,我尽量克制自己急促的呼吸,隐藏在芦苇丛中。她的长发披散在洁净的水中,舒展着四肢。过了许久,直到我都快站麻了,她才慢慢上岸。我先是看到她赤裸的背脊,两块小巧的肩胛骨支撑起一个奇妙的几何形状。然后,她的腰肢和大腿直至全部身体都象一只剥了壳的新鲜龙虾般一览无遗地暴露在河岸上。她的体形犹如两个连接在一起的纺锤。沾满池水的皮肤被月光照着反射出一种金色的柔光。
我终于看清了她的脸。
——香香。
她虽然只有十八岁,但脸和身体看上去都象是二十出头的女子。
她穿上了衣服,把所有的诱惑都严严实实地包裹了起来。然后她轻轻地说了一句:“出来吧。”
躲在芦苇中的我脸上象烧了起来一样,不知所措地磨蹭了一会儿才慢慢地走出来。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心头砰砰地乱跳,我有些害怕,她也许会告发我,把我当作有什么不良企图。
“对不起,我刚到这里,什么都没看见。”我想辩解,却越来越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
“你看到了。你全都看到了。”香香靠近了我,我的鼻孔里充满了她的气味。
“我不是故意的。”我后退了一步。
“别害怕。”她突然笑了,笑声在夜空里荡漾着,撞到风中摇晃的芦苇上,我似乎能听到某种回音。
“香香,你真的不会告发我?”
“你想到哪里去了,你当然不是故意的。你不是那种人。”香香赤着脚坐在了一块干净的地上,对我说,“来,你也坐下吧。”
我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坐在了她面前,却一言不发。
“你说话啊。”她催促着我。
“我——”我一向拙于言辞的,坐在她面前,鼻子里全是她身上的香味,我差点成了木头人。
“是不是睡不着觉?”
我点了点头。
“我也是。”忽然她对我做了一个禁声的动作,“听。”
四周一片寂静,连风也停了。
“听什么?”我摇了摇头。
“嘘,又来了,听——”
“什么都没听到。”我的听力还可以的啊。
“嗯,现在没有了,那个人过去了。”
“哪个人?谁过去了?”
“你刚才真的没听见吗?是拖鞋的声音,快听——嗒——嗒——嗒,从泥地里走过的声音,我听的很清楚,这么清楚的声音你怎么没听到?”她睁大了眼睛问我,此刻从她嘴里出来的声音让我毛骨竦然。
这时候,风又起来了,芦苇摇晃,我听了香香的话突然有些害怕,我站了起来,向四周张望了片刻,不可能的,不可能出现那种拖鞋的声音,一个人也没有啊。我想去芦苇的深处看看。
“别去。”香香叫住了我,“今天下午我听这里的乡下人说,许多年前,这块池塘淹死过一个来插队落户的女知青,他们说,从此每天晚上,这里的水边都会有拖鞋的声音响起,因为那个女知青是穿着拖鞋淹死的。”
“可我怎么没听到。”但我的心却开始越跳越快。
“乡下人说,一般人是听不到的,而如果有人听到,那么这个人很快就会死的。”她幽幽地说。
“别信那些鬼话。”
“呵呵,我才不会信呢,我是骗你的,不过我真的听到了那种拖鞋的声音。”
“我们回去吧。”我真的有些怕了。
我们绕过那条小河,拨开芦苇,向我们的帐篷走去,突然她停了下来,抬起头看着深蓝色的天空。
“又怎么了?”我问她。
“真美啊。”她还是看着夜空。
“什么真美?”
“流星。我刚才看到了一颗流星,从我的头顶飞过去。”她无限向往地说。
“你运气真好。”我看着天空,心里觉得很遗憾。
回到了营地,我们钻进了各自的帐篷。
那晚,我梦见了一个穿着拖鞋,梳着两根小辫子的女知青。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一钻出帐篷就看到了香香,她向我笑了笑,我也向她笑了笑。
后来,我们分开来自由活动,许多人去了海边,我也去了,回来以后,我们发觉香香不见了,她好象没有去海边。我们到处找她,始终没有找到,一直到了晚上,大家都非常着急,有的人急得哭了,我们向当地人借了煤油灯和手电继续寻找。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地方,于是,我带着大家去了昨天晚上香香游泳的那个小池塘,当我们来到芦苇深处的水边,用手电照亮了水面,在微暗的光线里,我见到水面上漂浮着什么东西。我有了种不祥的预感,我冲到了水边,闻到了一股香味。
漂浮在水面上的是香香。
几个会游泳的男生跳下了池塘,他们把香香捞上了岸。
香香死了。
她平静地躺在岸上,闭着双眼,似乎睡着了,而昨天晚上,她还在这里对我说她听到的声音。我想起了她的那些话,我的眼泪扑簌扑簌地滑落在了地上。当香香被抬走以后,我一个人留在了这里,这里的夜晚静悄悄,我一点都不害怕了,我非常渴望,能够听到那拖鞋的声音的,但是,我什么都没听到。
香香的验尸报告说她是溺水身亡的。可香香的水性是我们这些人里最好的,没有人能够理解。根据规定,香香的遗体必须在当地火化,我们都参加了她的追悼会,在追悼会上,我走过她的玻璃棺材,看着静静地躺在里面的香香的脸,我似乎还能闻到那股香味。
香香,香香,香香。
我想她。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时光倒流,让她再活过来。
我知道这不可能。
每年的清明和冬至,我都会到她的墓前送上一束鲜花。
现在,她的脸又清晰了起来,还有,她的气味,重新使我的鼻子获得了满足。
因为ROSE。
二月十六日
南湖中学位于一大群老房子的中心,从空中俯看就象是一片低矮的灌木中间被某种动物破坏掉了一块,那空白的一块就是中学的操场。
我和叶萧走进这栋五十年代建造的苏联式教学大楼,在空旷高大的走廊中,我们通过这里的校长,来到了档案室。1966年的档案很齐全,但是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用。
老校长喋喋不休地说:“红卫兵之类的内容是不会进入档案和学籍卡的。那一年有几百个学生加入了红卫兵,他们分成了几十批去各个单位‘闹革命’,要想查出哪些人去了南湖路125号简直是大海捞针。”
“那这里还有什么人熟悉当时的情况?”
“这个嘛,过去那些老教师都退休了,现在一时也找不到。恐怕有点难度。”
突然负责档案室的中年女人插了一句话:“校长,教历史的于老师过去不是我们学校66届的毕业生吗?”
“哦,对,我带你们去找他。”
校长带着我们走出档案室,在一间办公室里,校长对着一个正埋头看书的中年男子说:“老于,你不是我们学校66届的毕业生吗,市公安局的同志想调查一下66年我们学校红卫兵的一些情况。”
于老师抬起了头,他的神色突然变得紧张起来,他看了看我们,然后表情又平和了下来,淡淡地说:“校长,三十多年前的事,我都记不清了。”
校长对我们摇了摇头,轻轻地对我说:“你们别介意,他平时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性格内向,不太喜欢和别人说话。”
叶萧向我示意地点了点头,然后说:“于老师,能不能耽误你一点时间,我们到外面去谈谈。”
“我正在备课呢。”他有些不耐烦了。
“对不起,我正在办案。”叶萧直视着他的眼睛。
他们对视了一会儿,最后,于老师的目光避开了他:“好的,我们出去谈吧。”接着他又对校长说:“校长,你回去忙吧,我会配合的。”
穿过阴暗的走廊里,我们来到了操场边上,阳光懒洋洋地照着我的脸,一群上体育课的学生正在自由活动。叶萧抢先开口了:“于老师,1966年你是红卫兵吗?”
“是,但这重要吗?当时几乎每个学生都是。”
“对不起,你也许误解我们了,我们只是来调查一些事的。你知道南湖路125号这个地方吗?”
“黑房子?”他突然轻声地,几乎是自言自语地冒出来一句。
“什么是黑房子?”我问他。
他不回答,长长地叹出了一口气,然后看了看四周,把我们带到操场最安静的角落里,那里种着几棵大水衫,还有一些无花果树,地上长满了野草。在树荫下,阳光象星点一样洒在我们的额头,他缓缓地说:“因为那里是一栋黑色的楼房,十分特别,我小时候就住在那儿附近,所以我们那时候都把那地方叫做黑房子。”
“我们就是为了这栋房子而来的,于老师,我想你一定知道些什么,把你知道的全告诉我们,要全部。”叶萧说。
“1966年的秋天,我是这所学校里毕业班的学生,我们绝大部分同学都成为了红卫兵,批斗老师,搞大字报大辩论,但是许多人感到在学校里闹还不过瘾,于是有一群红卫兵去了黑房子。而我,也是其中的一员。”他突然停顿了,在我们目光的催促下,他才重新说起来,“你们年轻人不会理解当时的情况的,每个人都象疯了一样,尤其是十六七岁的学生,有许多事,需要时间才能让我们明白。我们去黑房子,因为那里是一个有许多知识分子的事业单位,据说是什么走资派的大本营。我们进去把里面的工作人员都给赶了出来,没人敢反抗,我们在所有的房间里都写上了大字报。最后,只剩下了地下室。我们命令看门的打开地下室,然后我们下去,那个地下室非常深,我们走台阶走了很久,回想起来挺吓人的,但是少年人有着强烈的好奇心,红卫兵又号称天不怕地不怕,终于,我们壮着胆子下到了地下室里。我们发现了一个玻璃棺材,在玻璃棺材里,躺着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
我倒吸了一口冷气,果然,1945年以后,皇后的遗体留在了地下室里。我再看了看于老师的脸,他的双眉紧锁在了一起,低下了头。
“继续说吧。”
“当时我们非常惊讶,一方面因为我们还小,不懂女人,一下子看到一个如此美丽的女人一丝不挂躺在玻璃棺材里,与其说是害怕,不如说是惊喜。是的,她太美了,我一生都没有见过那么漂亮的女人,大约20岁出头的样子吧,浑身雪白,闭着眼睛,安详地睡着。
一开始我们还真的以为她是在睡觉,我们有些害羞,想躲出去,后来有人说,一个女人脱光了衣服睡在这里肯定是个女流氓,要对她实施无产阶级专政。于是,我们打开了玻璃棺材,叫她起来,但是她却没有反应,我们中的一个人大着胆子碰了碰她,却发觉她的身上是冷的,再摸了摸脉搏,才知道原来她已经死了。一下子我们变得害怕起来,我们开始猜测她会不会是被人谋杀的,但实在也想不出什么结果,我们不敢把这件事说出去,因为我们看见了裸体的女人,也许会被别人认为我们也是流氓。我们只能例行公事一般在墙上涮上了大字报的标语,然后离开了地下室。”
“就这么简单?”我怀疑他还藏了些什么。
“不,当时我们白天在黑房子里闹所谓的革命,晚上还照样回家睡觉,毕竟我们还是孩子。进入地下室以后的第二天早上,我们象往常一样在黑房子门口集合,但是发觉少了一个人,叫刘卫忠,于是我们到他家去找他。到了他家里才知道,刘卫忠昨天晚上喝了一瓶老鼠药自杀身亡了。而昨天,只有他摸过地下室里的女人。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感到非常害怕,我离开了他们跑回到家里,再也不敢去黑房子了,那天我在家里窝了一整天,提心吊胆的。到了晚上,十点多了,我已经睡下了,突然张红军到我家里来了,他也是红卫兵,昨天也和我们一块去过地下室。他说他很害怕,晚上做恶梦睡不着觉,所以来找我,他告诉我一件事:昨天晚上,他和刘卫忠两个人偷偷地去过黑房子,他们发觉看门的人已经逃走了,大门开着,于是他们进去下到了地下室里。张红军说,他去地下室只是想摸摸那个女人,因为刘卫忠说这种感觉很舒服,他是在刘卫忠的鼓动下才去的,他说在地下室里,他们摸了那个女人的身体。”
“只是摸吗?”叶萧突然打断了他的话。
“我知道你想到了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就喜欢胡思乱想,那时候的我们很单纯,能摸一摸女人就已经被认为是大逆不道了。”
“对不起,请继续说。”
“那晚张红军说,他没想到刘卫忠会自杀,一点预兆都没有。我问他这件事情还告诉过谁,他起初不肯说,后来才告诉我,下午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件事说给那些去过地下室的红卫兵听了。后来实在太晚了,那时候的人们睡的都很早,张红军被我父亲赶走了。
第二天,我还是没有去黑房子,我对那里产生了深深的恐惧,我去了学校,清晨的校园里没有一个人来上课,我在操场里转了转想呼吸新鲜空气。但是,我在操场上发现了张红军,对,就在这里,就是现在我们站着的地方。他就躺在我们脚下的这块地方,口吐白沫,手里拿着一瓶农药。”他痛苦地低下了头,看着这片杂草丛生的地面,“当时的验尸报告说他是在那天凌晨三点钟左右喝农药自杀的。也许我永远都无法理解他和刘卫忠自杀的原因。”
我的脚下忽然生起一股冰凉的感觉,我急忙后退了几步,我真没想到,1966年,我鞋子底下的这块地方居然死过人。
“那么其他人呢?”叶萧继续问。
“以后他们的事我就不知道了,张红军死了以后,我再也没有参加红卫兵的任何活动了,不久以后,我就离开了上海,去云南上山下乡了。后来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以后,我考上了大学,毕业后成为了一名教师,被分配到了我的母校教书,一直到现在。”
“就这些吗?”
“我知道的全是这些了,那么多年来,我每次要路过黑房子的时候,总是绕道而行,尽量不看到它,那是一场恶梦,我一直生活在这阴影中。”从他痛苦的脸,我可以看出他的确没说谎。
“谢谢。能不能告诉我当时去过地下室的其他人的名字。”
“还好我一直记得他们。”他拿出纸和笔,写下了十几个名字,然后把纸交给了叶萧。
“非常好,谢谢你的配合,再见。”我们刚要走,于老师突然叫住了我们:“对不起,我想知道,你们去过那个地下室吗?”
“去过。”
“那个女人还在吗?应该已经成为一堆枯骨了。”于老师说。
“不,她已经不在了,但是,她不会变成枯骨,她永远是她。”我回答了一句。
我能看到他惊恐的眼神。
二月十七日
我又梦见了香香。
我实在在家里呆不住,我出去了,天色已晚,我在上海的街头游荡着。不知逛了多远,我突然看到眼前矗立着那尊有名的普希金雕像。看到沉思的诗人,我知道我该去哪儿了,又穿过两条马路,我拐进那条小巷,走进小楼,在三楼的一扇门前停了下来。
但愿ROSE在家。
天哪,黄韵的脸又浮现了,我承认我是个容易遗忘过去的,和所有的男子一样喜新厌旧的人,但是,我永远无法遗忘的是香香。
我敲了敲门。门开了,是ROSE。她很吃惊,然后对我笑了起来。她的房间还是我上次见到的老样子。只是电脑开着,一个系统软件的界面。
“请坐啊,你怎么会来?”她坐在一张摇椅上。
“顺便路过而已。”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路过。
“你撒谎。呵呵,你一撒谎就会脸红。”她轻轻的笑声塞满了我的耳朵,还有那股熟悉的香味。
我摸摸自己的脸,挺热的,的确是红了,我想转移话题,把目光盯着电脑问:“你在玩什么呢?”
“我在编一个程序,我被那家网络公司录取了。”
“恭喜你了。”
“没什么啦,就是编辑一些防范黑客和病毒的软件而已。”
我又没话了,好不容易才想出一句:“谢谢你上次送我回家。”
“我可不想让你在仙踪林茶坊里过夜。那天你到底睡着了没有?”
“没有,回到家以后才睡着的。”
“哦,那你还知道啊,别看你人瘦,扶着你还挺吃力的。”
“真不好意思,我怎么会那么狼狈呢,你可别以为我有什么病啊,我挺健康的,过去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真搞不懂。ROSE,为什么我看你摇来摇去,就有一种摆钟摇晃,时间停顿的感觉,然后我的眼皮就跟着你动了起来。”
ROSE把双手向我一摊:“我可不知道。”
“你能不能再试试?”
“随便你。”她坐在她的摇椅上晃了起来,就和上次在仙踪林里一样。一前一后,她的脸离我一近一远,从清晰到模糊,再从模糊到清晰,甚至连她的那股天生的香味,也随着她的摇动而一浓一淡。我的眼皮再次被她控制,我的视线从明亮到昏暗,再从昏暗到明亮,在明亮和昏暗的中间,是她的眼睛。
但我的意志是清晰的。
是时候了,我必须要说出口,这两个字在我心里酝酿了酗酒,终于,两眼无神的我对ROSE轻轻地说:“香香,香香,香香。”
ROSE的眼睛明亮了些,我能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一些别的东西,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我听到了她的回答:“听——”
我半梦半醒地回答:“听什么?”
“嘘,又来了,听——”
“我只听到你的声音。”房间里没有任何其他的声音,我的视线有些糊涂,但我的耳朵还完全正常。
“嗯,现在没有了,那个人过去了。”
“哪个人?谁过去了?”
“你刚才真的没听见吗?是拖鞋的声音,快听——嗒——嗒——嗒,从泥地里走过的声音,我听的很清楚的,这么清楚的声音你怎么没听到?”
天哪,这些几句话怎么这么熟悉,在我的记忆深处锁了许多年了,那些痛苦的回忆。没错,那是香香说过的话,那天晚上,在池塘边上,芦苇荡里,在她死的前一夜。
怎么从ROSE的嘴里说出来了?
她继续说:“今天下午我听这里的乡下人说,许多年前,这块池塘淹死过一个来插队落户的女知青,他们说,从此每天晚上,这里的水边都会有拖鞋的声音响起,因为那个女知青是穿着拖鞋淹死的。”
怎么回事,难道时光真的倒流了?难道这里不是ROSE的家,而是在十八岁时的苏北芦苇荡中的一个夜晚。
她还在继续,声音越来越低缓:“乡下人说,一般人是听不到的,而如果有人听到,那么这个人很快就会死的。”
我静静地听着,我的眼皮一闭一合,但我的耳朵听得清清楚楚,绝不会听错。我快疯了。我知道,还有一句话——
“呵呵,我才不会信呢,我是骗你的,不过我真的听到了那种拖鞋的声音。”ROSE把这最后一句话说了出来。
然后,她停止了摇晃。
我的眼皮恢复了正常,我睁大着眼睛,看着她,没错,她是香香。她就是香香。她的眼睛,她的脸,她的香味,她说的话,每一样,她都是香香。
“ROSE,你到底叫什么名字。”我靠近了她,双眼直逼着她。
她呡了呡嘴唇,幽幽地说:“我叫香香。”
“请再说一遍。”我有些痛苦。
“香香,我叫香香。”
我在发抖,我不知道我应该高兴还是害怕,我只知道,香香已经死了,我亲眼看到过她的遗体,她确确实实地已经死了,已经在那个苏北小镇上火化了,我理解不了,我痛苦地说:“这不可能。”
“世界上没有不可能的事。”她靠近了我,她的香味刺激着我,“我回来了,我从那个池塘里游了出来,我上了岸,我自己回了家,我考上了大学,我大学又毕了业,我工作了,我又遇见了你——我所爱的人。”
听到了她的最后一句话,我所有的防线都崩溃了,我的内心决堤了,是的,我承认,她是香香,她绝对是香香,没人能冒充的了。我的香香,我的香香又活了回来,我的香香没有死,她没有死。香香就是ROSE,ROSE就是香香。
我开始相信了她的话,生命是可以永存的。
我相信了复活。
我相信了时间的黑洞。
现在,我的香香就在我的面前,她靠近了我,她和我在一起,没有别人,我忍耐了那么久,因为我有一个强烈的冲动,我要得到她。过去我以为我永远都得不到她了,现在我知道我错了,我还可以得到她,拥有她,就是现在。
让这个世界崩溃吧,只有我,和她。
香香,我来了。
这一晚,我和她,完成了我们应该完成的一切。
她很快乐。
一切结束以后,在幽暗柔和的灯光下,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当我的目光触及她光滑的腹部的时候,我看到了一道淡淡的伤痕,淡红色的,象是一条直线似地镶嵌在白色的皮肤上。
我把头垫在她柔软的腹部,闻着那股香味,象个刚出生的孩子一样睡着了。
我睡得很熟,很熟。
二月十八日
我的耳朵里听到了鸟叫,各种各样的鸟,我醒了,我知道清晨到了。我睁开眼睛,看到了蓝蓝的天空。
多美的天空啊。
我感到了有点不对劲,怎么早晨睁开眼睛,看到的不是天花板而是天空。我支起了上半身,我看到自己正躺在一张绿色的长椅上,我的四周是树林,眼前是一条林间小径。我穿着衣服,衣服外面还盖着一条毛毯,我发觉自己身上有些湿,我用手一摸,全是清晨的露水。
“香香。”我喊了一声。没人回答,只有鸟儿在叫。
怎么回事?我站起来,看着周围的一切,一个人影都没有,我再看了看表,才早上六点半。
我想起了昨晚发生的事,我去了ROSE的家里,她承认她就是我的香香,我得到了她。然后,我头枕着香香的身体睡着了。
这一切是真实的,不是我的幻想,而是确确实实发生过的事,就在昨晚。
可是,现在又是怎么回事,我应该躺在香香的床上,看着她,看着她家的天花板和窗户。而此刻,当我醒来,却发现自己独自一人盖着条毛毯躺在小树林里的长椅上,就象个流浪汉。
我要去找香香。
我抓起毛毯,离开了这片小树林,穿过林间小径,惊起了几只飞鸟,它们扑扇着翅膀,发出羽毛的声响飞向天空。清晨的林间笼罩着一层薄雾,我踏着露水走上了一条更宽阔些的石子路。这里还有一个池塘,有些红色的鱼正在水里游着,我通过一座跨越池塘的木桥,看到了一堵围墙。透过围墙,我能看到墙外面的几栋高层建筑。还好,我现在至少可以确定自己不是在荒郊野外了。
沿着围墙,我见到了一扇门,门关着,我打不开,我明白,这里应该是一个市区的小公园。我在一片树丛里等了一个多小时,公园终于开门了,我从大门里走了出去,公园卖票的人显然大吃一惊,他来不及叫我停下来,我已经走到马路上了。
我看了看路牌,这里应该是徐汇区,离香香的家不远。
我来到了昨晚我来过的地方,宽阔的巷子,一栋小楼的三层,我敲了门。
没人开门。
再敲,我敲了很久,整栋小楼都可以听到我急促有力的敲门声。也许她出去了?
忽然隔壁另外一扇门打开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走了出来。
“别敲了,你是来租房子的吧。”老太婆说。
“不是,我是来找人的。”
“你是说那个小姑娘啊,她今天早上已经搬走了。”
“这怎么可能,昨天晚上——”后面那句“我还在这里过夜”的话我没敢说出来。
“搬走了就是搬走了,今天早上八点,搬场公司来搬走的,她还给我结清了房租。你不信我开门给你看看。”说着,老太婆从掏出了一串钥匙打开了门。
我冲了进去,房间里空空荡荡的,什么都没留下,房间里只剩下一股淡淡的香味,没错,我不会记错的,我还记得这里墙壁和天花板,就是这里。
她为什么搬走呢?
“阿婆,请问你知不知她搬到哪里去了。”
“我哪里知道。”老太婆不耐烦地回答。
“那么她是什么时候租这房子的?”
“去年九月吧。”
“那她在这里租房子是不是该到派出所去登记的?”我知道这个可能性不大,尽管的确有这样的规定。
“喂,你什么意思啊,你是来查户口的啊,去去去,”老太婆把我向外推了一把,接着嘴里嘟嘟囔囔地:“小赤佬,不正经。”
我知道在这里是问不出什么了,我走出了这栋小楼,再回头望望那个小阳台,我突然感到了自己的无助。
香香,你在哪里?
二月十九日
今天我的脑子里全是香香。
我坐卧不安,细细思量着前天晚上和昨天早上发生的一切,但我却丝毫无法理解香香为什么要这么做。她就象一个谜,突然地解开谜底,又突然地变成另一个谜。
我打开了电脑,上网。我先去了我常去的一家国内的大型综合网站,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闻,无非是些东剪西贴来的东西。当我要从首页退出时,我忽然发现左下角的友情链接里,发现了四个楷书字“古墓幽魂”。
不会搞错吧,怎么这里会有“古墓幽魂”的链接,要知道这家大型网站每天的浏览量有几百万,它的链接通常都是同样重要的著名网站,而古墓幽魂最多只能算是个人主页。会不会是其他同名的网站?我点了点链接地址,没错,的确是我所去过的那个古墓幽魂。
不行,我必须阻止他们,古墓幽魂放在著名网站的首页链结里,肯定会引来许多网友去登陆,也许会有更多的人遭遇不测。我立刻给该网站发了封MAIL,希望他们立刻停止链结古墓幽魂。
接着,我上了另一家国内的著名网站,令我吃惊的是,这家著名网站的首页里也有古墓幽魂的链接。接着我又换了一家国内大型网站,居然还是跟前面的一样。
忽然,我在这家网站的新闻里看到了一则报道——“神秘病毒袭击各大网站,首页链结遭到篡改”,我打开这则新闻读了读内容——“据国内各大网站的消息:日前,国内各大综合性门户网站,均遭到神秘病毒的攻击,所有被攻击的网站的首页链结的内容均被篡改,出现了一个叫古墓幽魂的链结站点。
据专业人士称,该网站系本市的一家个人主页,主题为中国的古墓,目前已经请求公安机关介入此事,具体详情不明,但至少可以确知的是,该病毒系通过黑客入侵者的方式传播,虽然被入侵的网站有严密的防范黑客系统,但是,入侵者具有更为高超的技术手段,轻而易举地修改了各网站的内部系统。各大网站的技术人员正在加紧努力修复被篡改的首页,但是目前为止,尚无法成功。但请网友不必担心,被篡改的仅为首页链结,不会影响到其他内容,网友的个人资料也未被黑客盗取。”
遭了,我早就料到古墓幽魂有某种极为高超的技术手段,但没想到它开始用病毒攻击各大网站了,通过这种方式,它可以使它的浏览量大幅度上升,简直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
当我胡思乱想的时候,门铃响了。
是叶萧。
从第一眼我就可以看出,今天的他的情绪似乎特别糟糕,他一进来,我就把网上的发生病毒事件告诉了他。他平静地点了点头说:“我已经知道了,前几天就发生了,我们动用了一切先进的技术手段,始终没能查出谁是古墓幽魂的策划者。我还尝试过删除其内容,也失败了,虽然地址应该就在本市,但是我们根本无法靠近它,怎么也找不到,就象是一个幻影。”
“的确象幻影,你曾经说过,那些不明不白的自杀者就象中了某种会传染的病毒。现在来看真的是病毒。”我担忧地说。
“是的,现在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似乎这些日子来,古墓幽魂的技术水平在不断提高,现在古墓幽魂可以通过病毒来篡改首页链结,将来就可以直接篡改各大网站的网页内容,到那时候,就会非常可怕了。”
我的脑子里瞬间浮现出一副图象,在一家国内著名网站的网页里,突然变成了黑色的屏幕,出现了一个骷髅,一个墓碑,还有清朝皇帝的画像,然后冒出一行字——“她在地宫里”。所有的网民都象那些自杀者一样沉迷于其中,最后全都——我想象不下去了。
真的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想些别的吧,我问叶萧:“你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些?”
“当然不是,上次我们在南湖中学,那个于老师给了我们一个1966年去过地下室的红卫兵的名单。我今天去户政档案部门查过这些名单上的人了。我复印了一份资料给你看看。”说着,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了一张纸递给了我。
“刘卫忠,男,生于1950年3月17日,1966年10月15日晚在家中服鼠药自杀身亡。”
“张红军,男,生于1950年1月26日,1966年10月17日凌晨在南湖中学操场服农药自杀身亡。”
“穆建国,男,生于1949年11月6日,1966年10月18日晚在南湖路上故意冲向疾驶的卡车身亡。”
“吴英雄,男,生于1950年5月15日,1966年10月19日凌晨在家中上吊自杀身亡。”
“张南举,男,生于1949年9月27日,1966年10月19日凌晨跳入苏州河自杀溺水身亡。”
“辛雄,男,生于1950年2月10日,1966年10月19日晚在家中服毒自杀身亡。”
“冯抗美,男,生于1950年6月18日,1966年10月20日凌晨在其父单位内割腕自杀身亡。”
“樊德,男,生于1949年12月2日,1966年10月23日晚在家中上吊自杀身亡。
“成叙安,男,生于1950年4月18日,1966年10月23日晚在南湖路上割腕自杀身亡。
“罗康明,男,生于1949年11月27日,1966年10月24日凌晨在一栋南湖路125号大楼上跳楼自杀身亡。”
“陈溪龙,男,生于1949年10月12日,1966年10月24日凌晨在家中上吊自杀身亡。”
“李红旗,男,生于1950年1月15日,1966年10月下旬失踪。”
“黄东海,男,生于1950年3月21日,1966年10月下旬失踪。”
看完了之后,我感到毛骨竦然,从1966年10月15日到10月24日,短短的九天的时间内,包括于老师说过的两个人在内,总共有十一个人自杀身亡,另有两人失踪,他们都去过地下室见过皇后,除了于老师没有继续去过那里以外,其他人都遭遇了不测。
叶萧缓缓地说:“你仔细地看,其中有两个死亡高峰,即从10月18日晚到10月20日凌晨,共死了五个人,10月21日和10月22日都没有死人,但是从10月
23日晚上到10月24日凌晨,其实只有一晚的时间,就又死了四个人。至于那失踪的两个人,我估计恐怕是死了以后没有找到尸体才被定性为失踪的。”
“这样说,所有的线索都断了?”
“差不多吧。”叶萧苦笑着说,“我决定放弃了。”
“你说什么?”
“放弃,我厌倦了,我厌倦了这一切,我不想再继续了。”他低下了头。
“我们努力了那么多,从古墓幽魂到东陵,到发现皇后的事情,再到现在,难道我们的努力都白费了。”
他不回答,沉默了许久,我也不说话,我的房间里死一般寂静。忽然他说话了,声音非常轻,低沉地吐出几个字:“我很害怕。”
“公安局的也会害怕?”我很奇怪。
“够了,我也是人,我真的很害怕,从一开始,我知道这案子,看到那些死者的资料,进入古墓幽魂的网站,去东陵,调查那些档案和资料,这些事情,每一分钟,我都是在极度恐惧中度过的。你不会理解的,我总是在表面上装出一付胸有成竹的样子,其实,我的心理比你还脆弱。”
“我要依靠你。”
“听着,每个人都有权利害怕。”他抬起头看着我,一字一顿地说着,他睁大着眼睛,额头冒着汗,那一副表情我从来没见过,我心中突然有些隐隐的恐惧,他会不会也——
叶萧继续说:“现在,我心理最后的防线终于崩溃了,我已经失去任何希望了,我想活下去,活下去,从一开始,我所谓的调查就是我的自作主张,现在是该退出的时候了。”
“你真的变了很多,我记得过去我们小的时候,你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害怕。”
“是的,我变了许多。你一定要知道原因吗?”
“如果你愿意告诉我的话。”
“那是恶梦,我不敢回忆的恶梦。我在北京读公安大学的时候,我谈过一个女朋友,是我的大学同学。我们谈得很好,在一起很开心,后来,我们毕业以前,去云南实习,跟着云南的一个缉毒队,我和我的女朋友也在一起,在一次缉毒行动中,不幸出现了意外,贩毒分子的力量要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我的女朋友被他们扣留了。
几天以后,我发现了我的女朋友的尸首。简直惨不忍睹,她被他们轮奸了,浑身上下到处都是被注射的针孔,他们给她注射了大量的海洛英,她是在极度的痛苦中死去的。当时在现场我逮捕了其中的一个毒贩,我把他拷了起来,用枪指着他的脑袋,我的女朋友的尸首就躺在我身边,我非常愤怒,我恨那些家伙,恨到了极点,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报仇,为她报仇。我差点就扳动扳机了,子弹将从枪口射出,把那个混蛋的脑浆给打出来,但是,在抠动扳机前的一瞬,我想到了——如果我开枪,那么我就违反了纪律,甚至违反了法律,因为他已经被抓住了,没有反抗,我不能打死他。
那个瞬间,我更加痛苦,我在报仇与执行公务间选择着,我真的非常想看到那家伙脑浆迸裂的样子,因为我的女朋友,我所深深爱着的人死得太惨了。最后,我没有开枪,我放下了枪,把他押回了警局。
后来,我总是给自己找许多理由,总是自我安慰说自己遵纪守法,其实我知道这些全是假的,我是因为害怕,我害怕,我害怕看到杀人,我害怕我被开除出公安,尽管我有报仇的冲动,但这种强烈的冲动在我的害怕面前居然一点作用都没有了。我害怕,真的害怕,也许在骨子里,我真的是一个胆小鬼。
所以,后来我没有参加刑警,而是在信息中心搞电脑,我再也没有碰过枪。就是这样,我变了,我发现了我心底深埋着的那种东西,那是害怕,是恐惧,天生的恐惧。而自从,发生了最近的这些怪事以来,我的恐惧就与日俱增了,我觉得那种害怕每夜都纠缠着我,我现在几乎每晚都要梦见我的女朋友死时的景象,我受不了。就这么简单。”
他哭了。从小到大,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眼泪。
“叶萧,对不起,我不该让你把这些痛苦的事情都说出来。”我想安慰他。
“好了,说出来就没事了。”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擦了擦眼泪,然后摇了摇头,站了起来,“我走了,我要回去早点睡觉,记住,别再管这件事了,我不想失去你,兄弟。”他抱住了我的肩膀,我们就象亲兄弟一样,我觉得我重新找回了小时候的那种感觉。
我送他出门,嘱咐他路上当心,然后我回到了房间里。
害怕。
什么是害怕,是恐惧吗?
我看了看那天ROSE(香香)送给我的白玫瑰。
玫瑰已经枯萎了。
二月二十日
我又上网了,几乎每个我上过的综合网站的首页里都能看到古墓幽魂的链结,一看到这四个字我就一点兴趣都没有了。于是,我一头钻进了我喜欢的一个论坛。
我发现今天几乎每一个贴子都只有五个字——“她在地宫里”。发贴人叫“古墓幽魂”。古墓幽魂在灌水?还是有人的恶作剧。我立刻发了一个贴子:“请版主删除所有的灌水贴子”。发完了以后,不可思议的是,我发现我的新贴子居然变成了“她在地宫里”,我的ID也变成了古墓幽魂。一定是服务器有问题,遭受病毒攻击了。
我该怎么办。
我关了电脑,静静地想了一个多小时,我想到了许多,想到了这两个月来所发生的这些匪疑所思的事情,还有那些死去的人,我看了看窗外,黑沉沉的夜色,就象冬至前夜的那晚,所有恶梦的开始。
也许还会有更多的人死去。
必须要阻止它。
我终于上了古墓幽魂。
首页还是老样子,不同的是浏览量发生了巨大变化——“您是第1072982名访问者”;“在线人数3197人”。我吓了一大跳,访问量居然超过一百万人次了,而上一次还是几万,看来古墓幽魂对各大网站的病毒攻击获得了显著的效果。
接着,我进入留言版,铺天盖地的贴子,我看了一会儿,全是些新来的人发的贴子,他们似乎都很兴奋,非常喜欢这里,许多人讨论如何玩最后那个迷宫游戏。然后我刷新了以下,又多出了十几条贴子,我再看了看点击数,一个一小时前的贴子,点击数已经超过了一百。真难以置信。
我再进入聊天室,还是一样,密密麻麻的名字,至少有一百多个,拉得我手都酸了。我不敢和他们对话了,我离开这里,进入了明清古墓中的清东陵。再进入惠陵,还是那五个字——“她在地宫里”。
进入迷宫。
系统还保留着我上次到达的地方,我继续前进。还是黑色的地道,前面一束微光,上下左右全是黑色石头砌成的,还有自己的脚步声。一个又一个分岔路口,我几次迎头“撞”上黑色的墙壁,音箱里传来非常逼真的“砰”的一声。我几乎能感觉到自己的额头产生了一种剧痛。我想到了这些天来我所看的那些资料,还有南湖路黑房子里那个地下室。
我的脑子里全是“地宫”这两个字,没错,现在电脑屏幕里的环境就是地宫,那天我下到地下室里时产生的恐惧与我现在的感觉是相同的。也许我真的离她越来越近了,我加快了速度,我觉得我越来越熟练了,我能非常有预见性地避开那些死胡同,如果我选择错了岔路,我就会七拐八弯地进入一个最终是没有出路的地道,然后我要再费很大的力气退回来。左面笼罩在地形图上的黑雾正在一步一步退去,一个小时以后,几乎已退去一半了。
忽然,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一个人影,那个人影越来越近,直到来到我面前,拦住了我的去路。难道又是叶萧?
我在下面的对话框里面打了几个字:你是叶萧吗?
接着对话框里的回答让我吃惊——
香香:我是香香。
我:香香,怎么是你,你怎么在这里,快离开,马上就离开。
香香:不,该离开的是你。
我:我不会走的,香香,你为什么离开了我。
香香:对不起,我有我自己的原因。
我:告诉我什么原因。
香香:你不能知道。
我:我想见你。
香香:现在见吧。
电脑屏幕里我面前的那个人逐渐地清晰了起来,黑色的雾气消失了,我看到了那个人的脸——香香。
音箱忽然响了,传出了香香的声音:“离开我,永远离开我。”
我继续在对话框里打字:不,我一定要找到你,无论你在天涯海角。
音箱沉默了片刻,接着又响了:“你不后悔?”
我:绝不后悔。
接着,电脑屏幕里香香的脸靠近了我,越来越近,直到整个屏幕都是她的脸,屏幕的中心是她红色的嘴唇,她的嘴唇有些变形了,就象是把嘴唇贴在了摄像机镜头上,我明白了,她在吻我,我能感觉到她嘴唇上的温度。
我也在电脑屏幕上吻了她的嘴唇。
瞬间,她的嘴唇消失了,她整个人也消失了,前方的地道里空空荡荡。
刚才也许是吻别。
我不后悔,我要找到她,我继续前进。我越来越感受到了地宫与墓室里的气氛,我知道那扇大门已经为我开启了,地形图里一大半的空间已经显露出来了,在地宫的中心,我知道,她在那儿。
我来了。
我终于闯进了地宫的中心。
那是一个巨大的空间,黑色的雾气笼罩着四周,头顶是黑色,脚下是黑色,前后左右都是黑色,在这黑色世界的中心,有两口硕大的黑色棺椁。
我点击了其中较大的一个棺材,棺盖打开了,我看到里面是一具穿着清朝皇帝龙袍的白色骷髅。
我知道,他是同治皇帝。
那么下一个呢?
我会看到什么?
我的鼠标移动到了第二个棺椁上面,停留了片刻,我的手指似乎不听我自己指挥了,僵硬了一会儿,终于,我深呼吸了一口,连着按了两记左键。
棺材盖打开了。
屏幕变成了一片黑色,在黑色的中心,出现了一只眼睛。
确切地说,是一个女人的眼睛。
我能到这只眼睛有长长的睫毛,乌黑的眼球,明亮的眸子,黑洞般的瞳孔。我又产生了那种感觉——这瞳孔象个无底洞,象个深深的水井。
灯灭了。
一瞬间,我房间里的灯灭了,全部的灯,包括电视机的电源灯也灭了,整个房间里一片漆黑。怎么回事,也许停电了?天哪,但愿只是停电而已。但我却感到了一种心底自发的恐惧,深深地渗透进了我全身每一寸皮肤,黑暗是恐惧的根源,陷入黑暗中,每个人心中,都会把自己深埋着的恐惧挖掘出来。我不想挖掘这恐惧的潜力,但我无法抗拒,我无能为力。但我又无法确知这恐惧到底在哪里,但我突然产生了一种直觉——恐惧就在我背后。
电脑屏幕里的那只眼睛消失了,而变成了一片灰色。
十几秒钟以后,灰色的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行字——看看你的身后。
我回过头去。
一个人影,我看到一个人影站在我的背后。
我把手放在了自己的胸口上,我能感到自己的心跳几乎要穿出自己胸膛了。我站了起来,借助着电脑屏幕里发出的微弱的灰色的光线,看着我身后的人影。
人影向前移动了一步,不是我的幻想,而是确确实实存在着的一个影子,而且是女人的影子,就在我的房间里,就在我的面前。
电脑屏幕灰色的光线照射在那个人的身上。
香香。
她全身穿着白色的衣服,脸色苍白,面无表情,我能感到她的身上发出一种寒冷的气息。
“香香。”我叫她。
她不回答,只盯着我看,几秒钟后,从她的嘴里,一字一顿地吐出几个字:“还——我——头——来——”
那不是她的声音,我确信,这绝对不是她的声音,无论是十八岁时候的香香,还是我的ROSE,都不是这个声音,而是另外一个女子的声音。这声音充满了哀怨,充满了仇恨,不象是从我的房间里的人发出来的,而是从地下发出的声音,就象是把自己的耳朵贴在地面上而听到的那种声音一样,异常地沉闷。
当她说完这四个字,突然,我房间里的灯全都亮了。
在这瞬间,她消失了。
我的眼睛刚从前面的黑暗中出来,还没恢复,我使劲地揉了揉眼睛,再看了看我的房间,她不见了,的的确确消失了,就象这空气,这光线一样。
我再看了看电脑,我的电脑居然已经自动关机了。
我长出了一口气,又坐了下来,我的额头上全是汗,我知道我刚才恐惧极了。我不敢再回想刚才发生的事情了。我匆忙地睡下了。
我梦见了一个女人。她有丰满的胸脯,修长的手臂和腿,白皙光滑的皮肤,惟独缺了一样——她的头。
一个没有头颅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