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石宕的抢劫
已阅读:525次
作者:须弥山主人
只是碍于老同学的情面,我才接下这个离婚案子的。下决心离婚的那个女人是我同学的远房表姐,据说挺漂亮,曾是什么学校的校花或哪个局的局花。她就住在紫石宕小区的边缘,离我家不算远。紫石宕事实上是城北的统称,包括北郊和部分城区。在我们城市,对住在紫石宕小区的人普遍缺乏好感,昔日那里曾聚居着本地的显贵,随着城市重心的转移,现在几乎已沦落为城市贫民的集中地了。我之所以辞职转行,在内心深处恐怕也与此有关,希望积聚一点财富,以便将来能搬到远离紫石宕的新区去住。
晚饭后我换了套淡黄色的连衫裙,带上黑色的小挎包,在紫石宕河北边的小路上散步。天色阴阴的,西天乱叠着一些淡红的云霞,空气稍有点闷。铁路那边的西瓜田里,有几个人围在一起高声谈论,旁边的小卡车装满了西瓜。看见我,一个光头青年打了个唿哨,做着吃西瓜的动作,还怪模怪样的啧味道,别的人都哈哈大笑。我自然不予理睬,沿铁路走了半个多小时,过桥回到城区,从紫石宕路步行去同学的表姐家。
如我所料,我的当事人情绪激动,没说两句就哭哭啼啼起来。这种场面我见得多了。我感兴趣的是重大经济纠纷,最烦的就是这类事。但既然来了,我只好一边在心里抱怨老同学,一边对她的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一边了解情况,调查取证。她的故事无非是这样的:那个她倾心爱着的丈夫捞到一官半职后,就开始在外面寻花问柳夜不归宿,导致感情破裂,他甚至转移家庭财产,暗中作好撤离婚姻的准备。他当然同意离婚,但要取得孩子的抚养权。她在叙述中还多次提到她的表弟的名字,似乎这个名字是一个符咒,能让我的同情心和工作能力都加倍。其实我此刻心里最恨的就是她那位胡乱介绍案子的表弟,而且她那种事我见得多了,依我的想法,放弃孩子抚养权,争回点财产就得了,像她这样容貌不恶的女人,没有孩子的拖累,说不定还能找个不错的丈夫。但她一定要孩子,态度坚决到咬牙切齿的地步。一个女人能退守到哪里?只能到孩子为止。这我理解,心里就有点儿不好受。这样的事我确实看得多了,但总会使我难受。其实打动我的不是她那种可悲的遭遇,而是她的痛苦。
那个被争夺的孩子是个阴沉的小男孩,十一二岁光景,他闷闷不乐地看完动画片,就开始拆一辆玩具汽车,将零件扔得满地都是,有一个轮子还飞进了我的茶杯。他吃了母亲的一个耳光后,一声不响地躲进自己的小房间里去了。我发现他的眼神对我充满敌意,似乎是我使他的家庭面临破裂局面的。这孩子自己愿意跟谁过日子呢?我想他当然希望选择与父母一起过,但他的父母不让他这样选择了,他的选择多不自由啊。
她哭哭闹闹,又是诅咒又是发誓,直弄到深夜11时事情才算告一个段落。我起身告辞,她收起泪送我到门口,又紧紧拉住我的手,恳求我无论如何要帮她将孩子夺到手,说孩子若跟着那样狼心狗肺的人过,也非变成狼心狗肺不可,长大了不知道会害了多少人。没说几句又声泪俱下起来,好像看到了她儿子不妙的前景。我急于回家,并没有被她这种深谋远虑折服,当然也没有摔脱她的手,只是劝她多多保重,顾眼前要紧,劝得我自己也鼻子发酸。这样又说了半个小时,我才得以脱身。
我二十岁左右那会儿,这条幽静的紫石宕路在小城的年轻人中很出名。那时候我们城市只有几个规模很小的路边公园,紫石宕路比那些小公园撮成了更多的婚姻,一对青年男女在这条路上走,就意味着他们在走向婚姻,至少是他们有这种企图。所以它有个冗长的别名叫做“一千五百米爱情线”。现在它和紫石宕小区一起没落了,显得更加幽静。城市向三个方向拓展,唯独不在这个方向蚕食农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路上我走得很慢,我可不想将心烦带回家里。我不是个工作狂,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当妻子和当律师同样重要,不能搅在一起,更不能颠倒。这是我一贯的原则。当别人称赞我办事干练得体什么的,我以为可能正是由于这样的处事方式。我有一个朋友,是小学教师,她做事正好相反,常常将作业本带到家里批改,这肯定影响生活,我担心她有朝一日会忘乎所以地在教室里结毛衣或剥蚕豆,或者对着丈夫讲解课文。所以我至少在回家的路上要将工作都打理一遍,放置在脑子的某个角落里,暂时不去管它。这不难。毕竟是深夜,行人很少,偶尔也有人骑着自行车超过我,在残缺不全的路灯光下,他们的影子像幽灵似的忽明忽暗,好像是从路边一个无形的屏幕上经过。有两三个骑车的人还回头看了我一眼。我知道他们可能是将我当作那种女人了。这使我很恼火,我猜想他们用的眼光可能是下流的、憎恶的,也可能是同情的,不管是哪种,都使我恼火,就在心里驳斥他们的眼光,举出与那种女人的许多种区别,所以直到经过城市边缘紫石宕河上的虹影桥时,才发现有人不知什么时候跟上了我。那人的脚步很轻,几乎有点儿蹑手蹑脚。我不希望学过的防身术真的派上用场,心想他也可能不过是碰巧和我同路,但我还是心情紧张,不由得呼吸急促,加快脚步。后面的脚步声也急促起来,并渐渐接近。
路的左边隔着围墙是一排排灰色的楼房,毫无生气地隐藏在夜色里,每扇窗子都黑黑的。右边是发臭的河,路与河之间是一排叶子过于密集的梧桐树,河那边的田野、村庄和铁路,在黑暗中无法看清,只有虫子的鸣叫声不停地传来。我的高跟鞋着地发出响亮的声音,在寂静中分外刺耳,好像在与身后的脚步声作虚张声势的争辩。
我偷偷试演了一个防身招术,发现动作僵硬生疏,双臂根本不听使唤,两只手掌却不自觉地微微颤抖,手心也已经热得发潮。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也越来越轻,简直是踮起了脚尖,每一声都像踩在我的心上。我脊背上的汗毛像草一样蓬勃竖起,草尖触到那一大团悬挂在背后的黑暗,让人心里阵阵发虚,觉得再也没有勇气相持下去。我一边想象着自己猛回身抡起挎包尖叫着摔出去的情形,一边偷偷回头瞥了一眼,不禁在心里打了一个突:身后空空荡荡的,根本没有人,连影子也没有,只有一条路,还有风。这远比看见一个相貌凶恶的歹徒更使人毛骨竦然,我全身有些发软。道路在微明的灯光下难以分辨,灰蒙蒙的,虚假得像模糊的碳精画。沙沙作响的风吹得我直打寒颤--我已满身冷汗,感到四周有无数双眼睛在偷看。
我定了定神,努力地笑笑,从容不迫地慢慢回头。就在这时,我眼前一黑,一只大手无声地搭上我的肩头,我的心突地一跳,一口冷气噎住了喉咙,接着看见一个高大的人影紧靠着我站着。他一声不响,脸也无法看清,身上发出一股混杂着霉味和烟味的奇怪气味,他的手捏得我肩膀发痛。我感到浑身乏力,虚脱了一般,喃喃地说,你想干什么?声音嘶哑飘浮,听上去像梦中的乌鸦叫声。他的喉咙里发出喀喀的声音,我没有听见他说话,又问,你想干什么?
一道亮光掠了过来,他反应迅捷,一把按住我的后脑勺,将我的脸用力按在他的胸口。我毫无防备,也不明白他想干什么,只闻到他衬衫上的一股霉味,然后就呼吸不出,脑袋混混沌沌,好像还听见有一辆车从身边驶过。我的挣扎就像蜻蜓撼石柱,丝毫不起作用。他突然放开我的后脑勺,我的脑袋不自禁地向后一仰,身子差点失去平衡。他抓紧我的肩顺势往路边带了几步,一只手粗暴地摸索我的手腕、手指和脖子,并扯住我的项链,另一只手抓住我的挎包。我的神志有点清醒过来,意识到面前是一个男人,而且是一个抢劫财物的歹徒,忙抓紧挎包,用拳头打他的手,急促地说:
带子要拉断了,带子要拉断了。
我不明白此时我最关心的为什么竟是挎包的带子。我学过的防身术毫不管用,既施展不出,也没想到要施展一下。
你说什么?他愣了愣,问。
也许与我那专门与人比赛说话的职业有关,听到他开口说话,不知怎么的心里就不大害怕,并很快镇定下来。我想,语言是一种武器,而我这方面的武器应该是比较精良的,我又想,他犯了一个错误,他说话了,这等于授我以柄。我壮起胆用劲掰他的手指,随口说道:我不喜欢这样的,你不知道,我不喜欢这样的,你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不知道?我感觉到他抢夺的动作缓慢下来。
我第一个想法是告诉他这是犯法的,并用我的律师身份威吓他。但我马上否定了,因为这只会使他害怕,人在害怕的时候容易铤而走险,说不定就对我下毒手。他是一个男人,当然有男人的弱点,所以我用一种假装害羞的口气说,我不喜欢这么快……这么快……我努力微笑地看着他的脸,一点儿也不向周围张望。跟你说吧,我与别的姑娘不大一样,不喜欢很快很直接的,太像做生意。
他抓着我的挎包,没有说话。我知道现在最危险的是沉默,只能继续假装不明白他的险恶用心,不停地说丰话,同时习惯性地从包里取出一片西瓜霜含片噙在口里。我明白即使我失身了,他还是会抢走我的所有东西,说不定还会杀了我。我得尽量拖延时间,分散他的注意力,否则一点机会也没有。虽然他看不清楚,但我还是又给他做了一个自以为灿烂的笑容,说,可能你不大习惯,可我想总得互相有个了解,找点情调,否则算什么啊?我轻轻抓住他的手,小心翼翼地移到身侧,让他挽住我的胳膊,征求他的意见:我们散一会儿步好不好?
他看上去有点拿不定主意,说,你甭想玩花样,这没用。
你怕我玩花样?我笑得弯下了腰,指着他说,什么花样?怕我吃了你?胆子那么小,白长那么大个儿!我挽着他慢慢移动脚步,你从不这样的?先散步,吃点消夜什么的,你怎么从不这样?干什么都得有个次序。
废话少说!他又开始在我的脖子里摸索。他是想找到项链的扣襻。我吃吃笑着,声音干涩,一边轻轻拨开他的手,说,心那么急干什么?一点情调也不懂,算什么男人?过去你和几个女人好过?
他生气地说,我像那样的人吗?我从不乱搞!
那今天怎么有兴致出来?我说。我意识到谈话的方向有点危险,如果他放弃接受女色的诱惑,很可能马上着手抢劫,那我就没有机会了。我们先去哪里吃点东西?
不吃。他说,我不饿。
可我有点饿了,你陪我去吃点儿吗。
我不饿,你也不饿。他说着短促地笑了一声,听上去像一颗石子掉落在地,立刻又用凶恶的口气说,别动脑筋了,没用的。
左边的围墙尽头是一个小弄堂,一缕灯光从弄堂口投射到这条路上,将路截成了两段,另一段隐没在黑暗中。那盏灯看上去比紫石宕路上所有的路灯加起来还亮。我侧过身子缓缓地向灯光走去。他似乎识破了我的用心,粗暴地拉住我,继续沿着紫石宕河走。经过弄堂口时他明显地快走了几步。灯光在我们身上一晃而过,我只来得及瞥见他有一张微黑的中年人的脸和一头乱糟糟的头发,眼角的余光似乎还看到他的西装是灰色的。我沮丧地想,如果我不是存心看他的脸,说不定还能看到更多的特征呢。
在我们这个不大的城市里,我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却窝窝囊囊地假扮成一个妓女被这下三滥的恶棍挟持,实在令人哭笑不得。现在我们行走的方向与我回家的方向一致,这多少给了我一点信心。只要到家门口就好办了,到时我要给他点颜色看看。被我送进监狱的人还少吗。但此刻我不敢掉以轻心,一个劲地说着话。我编了个故事,说我家里因为火灾欠下一大笔钱,还有一个读中学的弟弟和生病的母亲要供养,只好跑到外面来打工挣钱,没想到找工作这样难,身边的钱用光了,不得已干起这一行。我希望能用这个老套故事骗得他良心发现。
他没有出声,一边走路,一边用身体将我挤在河的一侧,右手绕过我的背部用力抓着我的右臂。我不知道我的故事是不是对他发生了作用,偷偷地看他的表情,但天太黑,只看见他脑袋的轮廓。他注意到我在看他,用低沉的声音说,你这种故事我早就听见过了。很多人都讲这样的破故事。他的右手放开我的手臂,接着一个锐利的东西顶住了我的腰部。他说,不许叫,一叫就没命。我吃惊地问,你干什么?话才出口就明白了,后面有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过来了。那是个小伙子,穿着一件白衬衫,超过我们时不经意地扭头看了一眼,又哼着歌继续赶路,自行车骑得飞快。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黑暗之中,心里升起一种苦涩的滋味:这个陌生小伙子,他根本不知道他也许是我唯一的救星。我又想,这个恶棍的耳朵倒蛮灵的,我怎么没听见声音呢,看来他确实挺难对付。这时我才突然发现:他根本没有相信过我的任何一句话,他听着我说话,和我一起走着,却半点也没相信过我,也就是说,他有自己的打算,他要拿我怎么办?如果他是一个惯犯,过去他拿别的人怎么办的?我想起先奸后杀,洗劫财物,分尸沉江等词语,但那样的可怕情形,却怎么也不敢想。
这个城市睡得好熟啊,我想,白天熙熙攘攘的人群,现在都分散到各自的家里安安稳稳地睡着,包括我的那个同学,他搂着他的妻子进入了梦乡,却没想到我快被他害死了。他的该死的表姐离婚关我什么屁事?我心里一阵气苦。
你这是干什么?我恨恨地说。
我只想让你放老实一点。他嘿的笑了一声。
什么东西,扎得我好痛。我用手摸了一下,受了惊吓般说,刀子,你拿刀子干什么!你是黑社会的是不是?你认不认识雷司令?
他妈的,你才是黑社会。
我知道了,你出来想买西瓜,没买到西瓜,就想找女人玩,你这种人我知道。
不是,我就爱带刀子,你怕了?
你收起来吧,这东西又不好玩。
他没有收起来,刀尖扎得我一痛一痛的,走路倒像是受刑。我想我穿上一件罩衫出来就好了,我本来应该想到的,初秋的深夜天气会变冷。紫石宕小区已远远抛在后面,通天桥已经过去,罗家桥新村的围墙也走完了,只有紫石宕河还在我们的左侧发臭。
三里亭新村到了。第四幢楼房的303室就是我的家,丈夫在家里等我。我不回去他是不会睡觉的。我注意到我家的窗口透出明暗变幻的光线,他在看电视。他真是好耐心啊,妻子那么晚还没回到家,他居然还有心思看鬼电视。他不会到窗口来张望一下?我与一个高个男人在路上搂着散步,他难道不在乎?我晚上出门,他应该陪我去才对,要不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狼心狗肺的东西,你窝在家里等吧,等我的尸体吧。
我的家就这样很快很平静地过去了,平静得连我自己也难以置信。我想,我这和在自己家门口被人劫持有什么两样?原来生活是这样的不安全。
前面是环城东路。到了环城东路,我总该有机会了吧,我想,那里肯定有人的,只要熬到环城东路,一遇到人我就挣扎叫喊,即使被他扎上一刀,也得逃脱他的魔掌。不然的话,谁知道他会带我到什么鬼地方去。环城东路,霓虹灯美丽动人,街灯的光芒明亮地交织着,那是我即将到达的天堂。我的脸上发热,脚步因兴奋而加快,心悬在喉咙口,几乎要蹦出来。他忽然捏住我的胳膊用力一推,我猝不及防,踉踉跄跄地几乎摔倒,发现已被他拉着拐入一座小木桥。我胸口一沉,一股寒意冒上心头,头皮发麻,脑袋晕乎乎的,身不由己地跟他越过紫石宕河。紫石宕河这条城区和农村的分界线,现在成了天堂和地狱的分界线,我知道,走过这座桥,我是死定了。我挣扎着说,你这人,怎么能……这样?他坚硬如铁的手又紧了紧,说,你不是想要情调吗?这里情调不错吧?我苦笑着说,不过我不喜欢……不喜欢在野地里……他打断我的话,你想到人多的地方是不是?你想叫别人来抓住我是不是?
脚踩着田塍上的草丛,发出细细的沙沙声,旁边有一匹小动物窜过,钻到一个黑乎乎的草堆里去了。我叹了口气,说,我从来没有被人带到这种地方来过。我想起我编的那个故事,又说,我在老家也有个男朋友,我们只是去镇上看两场电影,从来不去野地里。不过有的人是去的,比如我的一个好朋友,她和男朋友第一次好就在野外。
你和男朋友第一次好呢?他干笑着说,难道在旅馆里?我呸了一声,你胡说什么呀?唉,我们还来不及好,我家里就着火了,后来他就不理睬我了,就是我约他去看电影,他也总是推三阻四的不肯去。我有时想,如果我答应他,给了他,他会不会不理我。不过也无所谓,男人总是这样朝三暮四的。他哈哈大笑,说,人总是这样,你怪我我怪你,依我看,如果男人是朝三暮四,女人就是水性杨花,都一样的。
我低着头慢慢走着,沉思了一会儿,小心翼翼地说,你的老婆,你的老婆也水性杨花吗?他用力搡了我一把,大声骂道,放屁!你他妈的才是水性杨花的婊子!我拐了一下,摔倒在路边,委屈得哭出声来,我从来没被人这样骂过,这狗娘养的居然敢这样骂我!我拿出手帕擦着眼泪,提高声音说道,你这姑娘养的私生子,我愿意水性杨花吗?我不想好好地嫁个人过日子吗?我愿意家里着火吗?我爱当婊子吗?我坐在地上用力蹬着两腿,妈妈啊,你这该死的生我出来干什么?这世界婊子还不够多啊?我一边撒泼哭嚎,一边心里诧异:我竟还有这一手,演技不错啊,原来当泼妇这么容易,说不定每个女人身上都有泼妇的影子吧。
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弯腰拉我起来,说,好了好了,不要哭了,算我不对。我收住泪,小声说,你以后不可以再骂我的。他说,不骂不骂。
我们像一对重归于好的恋人一样并肩走着,我望着他的侧影说,你的脾气很好啊,你老婆会对你不好吗?他嗡声嗡气地说,谁说她对我不好?我冷笑一声,那你为什么跑出来偷荤?你这小没良心的。他厉声道,别说了!你不要生气嘛,哎,如果你没有老婆,会不会娶我?
什么?他吃了一惊,娶你?
对呀,我嗲声嗲气地说,不过你别笑,我知道你不会娶我的,像我这样的人,唉,我这辈子是没指望了,做过这种事,能嫁给谁啊。
我以为他会说“当然会娶你啊”之类的话与我开开玩笑,可是他没说,摸索一会儿,用火柴点上一支香烟,一边抽着,一边低着头走路,我甚至能感觉到他阴沉着脸,还在动着什么坏念头,心又开始怦怦乱跳。这时我突然发现我犯下一个弥天大错,我的包里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东西,就是连白金项链、金戒指全被他抢走,也不过值两三千元钱,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我却为了这一点点东西,落到了这样的危险之中,这简直是个黑色大幽默!我想起我经手过一些案例,有两个老头打麻将,为了争五元小钱,竟闹出了人命;还有一个人,不愿买两毛钱的公园门票,翻墙进去时掉下来,落得个终身残废,状告公园,又赔出诉讼费。我现在与这些人又有什么区别呢?我如果被他抢走一点什么,趁他不备一边逃一边喊救命,他胆子再大也不敢再追我吧。现在,我将自己扮成妓女,还自鸣得意,以为骗倒了他,却在不知不觉中身陷万劫不复的境地!明天人们发现我的尸体的时候,恐怕谁也不会想到,是我自己放弃了逃生的机会。我满心说不出的窝囊和后悔,都变成了满腔怒火,恨不得立时死掉才好。
我知道,你本来是个好姑娘。他犹豫着说。
放你妈的臭狗屁!我心情恶劣得像填了一肚子稻草,尖声叫道。
怎么了?我又说错了?他惊讶地说,我没有要讽刺你的意思,真的没有。
你有,你有,我大喊道,你讽刺挖苦,偏偏我根本不是你想的那种人,不是什么野鸡,我告诉你,我是一个律师!我的声音突然中断,“律师”两个字像一枚突然爆炸的炸弹,震得我耳朵嗡嗡直响,我感到一阵晕眩。我又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一认清我的真面目,用那双坚硬的大手对付我脆弱的脖子,不要五分钟就能叫我断气。
我知道我知道,他说,你当然是律师,你是个顶呱呱的律师。
他知道!怪不得他根本没相信过我的话,其实他早就知道我是谁--说不定他是某个被我送进监狱的罪犯,或者是罪犯的亲戚朋友,他是来报仇的,他碰上我不是偶然,而是蓄谋已久。他带我到这种偏僻的地方,居心险恶不言自明,他要怎样折辱我杀害我,也已策划得周周到到。我身子一软,倒了下去,脑袋里一片空白。
他及时扶住了我,阴恻恻地说,小心,这路不大好走。你知道我是谁?他搂着我的腰肢说,我是一个飞行员,开喷气式战斗机的飞行员。他停住脚步,拨动我的身子,让我面对着他,继续说,小孩子懂个屁……全不是这么回事,活着就是你想去什么地方,却偏偏让你往相反方向走,这我老早就弄明白了。
你是飞行员。我头冒虚汗,低着头抽泣道,你是真的飞行员。
不是,飞行员现在在天上,打着红灯绿灯黄灯,在天上飞,他笑起来,说,这话听上去像傻瓜。如果我真当上飞行员,说不定做人也一样没意思。
天上飘下零星小雨,落到脸上凉凉的。一只蝙蝠从头顶无声地掠过,在微茫的天光中能看到柔软的长翅展开着。天上没有飞机,也没有星星,只有城区的各色灯光,寡淡地涂抹了半边天空。虫子的叫声远远传来,听上去有一种压抑的热闹,令人不快。这时我们已经上了铁路,沿着铁路线走。怎么没意思呢?你做人也会没意思?
你刚才说过你愿意嫁给我是不是?你说过的。他又站住,面对着我说。
我知道你要笑话我,不许……
你说过的,是不是?你再说一遍。
好好好我说我说,我嘻嘻笑道,我愿意嫁你。
我知道你不是真的,他哈哈笑着说,我知道,我知道的。
当然不是真的,你当是真的?我奇怪地说,你有老婆,我有老……婆,再说,我是个这样的姑娘,你即使没有老婆,怎么会要我?
如果我没有老婆呢?
我突然意识到什么,心扑嗵一跳,从包里摸出一片西瓜霜含片塞入嘴里,用认真的口吻说,你真的会娶我?我不信。我不是自卑,你在玩我是不是?你在玩我。唉,像我这样的人……
你要怎样才相信?我是挺严肃的。
可我总觉得高攀不上……你不想我们再了解得深一点?这事太重大了。
他揽住我的腰,在我的额头轻轻吻了一下。他的双眼注视着我,在黑暗中发出一种黑光。沉默了一会儿,他说,你知道我这么晚了出来干什么?我不是来找乐子的,我是来抢东西的。
我啊地叫了一声。我知道他是来抢劫的,但没有料到他会自己说出来,在谈论那样的话题时突然之间说出来。他这就要跟我摊牌了!要动手了!我惊恐地看着他,结结巴巴地说:你怎能……怎能……
他打断我,飞快地说,你放心,我以后决不再抢了,做这种事,运气再好也会有失手的一天,我不会再做了。我们就过穷日子,找份工作,想办法帮你还债,供你弟弟读书,不过你也不能再做这种生意,你说好不好?可是……你老婆……
我确实没有老婆,他的手在空中虚劈了一下,我老婆跟我离婚了。她嫌我没出息,总是被人欺侮,我在单位里他们叫我什么?叫我糯米团子。他短促地笑了一声,我糯米团子,他们他妈的才是糯米团子呢,他们敢半夜里出来抢劫吗?嗤!他忽然激动起来,一边大步走着,一边说,我连白脸狼的老婆也抢过,白脸狼这狗娘养的,就会扣我工资,对人家说,扣吧,扣糯米团子吧,他屁都不敢放一个。他是狗娘养的,他跟老婆都被我抢了,他倒是屁都不敢放一个,你猜我怎么干的吗?我摘下她的项链戒指,掏空她的口袋,还当着那狗贼与他老婆亲了个嘴,他屁都不敢放一个,真他妈过瘾。我是糯米团子吗?我怕什么?我早两天就辞职了。他微仰着头,眼睛里闪着绿荧荧的光,脸上似乎还有笑容,黑暗中看不大清楚,显得很可怖。
白脸狼……没有报案?我迟疑着问。
不知道,他不敢报,我叫他蹲下,他乖乖蹲下,屁都不敢放一个。
为什么不敢报?
他愣了一下,忽然发起脾气,报他妈的大头鬼,我没强奸他的婊子老婆还算客气,他们一家人都是婊子!我操他十八代祖宗姥姥!突然顿住,呆了呆,说,我以后肯定不干这种事了,你要相信我,我老婆跟我离婚了,我想我完了……他歪过头看着我说,你问那么多干什么?你再多嘴看我掐死你,你以为你是谁?
我吃了一惊,退后两步,在铁轨上绊了一下,大着胆子说,人家只是怕你出事嘛,你那么凶干什么?认识你第一天就这样,我宁愿被你掐死。
我只是想起一些事,挺窝心的,他叹了口气说,我过去对老婆百依百顺,可她不知足,她总是不知足。离婚后我的生活一团糟,连工作也丢了--我要杀掉她,反正我也已被她害惨了,同归于尽吧,我要杀--当然了,现在不同了,我已懒得理睬她了。
他的故事几乎和我编的故事一样流行,他说他和妻子是中学同学,结婚后生活平淡,也没有孩子。后来妻子有了外遇,打算将那个第三者变成第二者,便开始有计划地与他吵闹打架,然后每天冷战,然后分居,最终离婚。她从来没有对我好过,他说,她从来只顾自己的。那个女人几乎搬空了家里所有东西,只留下一套两居室的房子。他感到非常绝望,每天关在徒有四壁的家里痛不欲生。他分析说,现在想起来,如果说他爱妻子真爱到这程度,那也不见得,他只是感到被彻底抛弃了,就自暴自弃。被一个女人抛弃,就是被全世界抛弃,这种情形下男人是看不到一丝希望的。他也没什么朋友,如果有朋友陪伴,说不定不会变成这样子。
总之,他像生活在黑暗深处,心情恶劣,神经衰弱,常在深更半夜出门,在街头徘徊游荡。有一天夜里遇到一个问路的女子,他想也不想抢走了她的坤包,那时街灯明亮,行人不少,那女子似乎被吓傻了,站在那里看着他消失在一条小巷里。这是他的第一次抢劫,事后想想对自己的胆大妄为尚有余悸,以为第二天会有满城警察追捕他。实际上他早将坤包丢在一个阴沟里,根本没有打开看过。但他的内心深处却感到一种隐秘的喜悦,似乎对妻子作了一次程度轻微的报复。这种报复以后多次发生,渐渐成了一种习惯。
没多久,这成了他的生活来源,白天睡觉,晚上出来游荡,生物钟也颠倒了,晚上无法合眼,面对空空的墙壁感到难以忍受。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出来后本想找个工作,可一连碰了三个灰鼻子,就索性重操旧业。
这个乏味的故事他讲得支离破碎,有时忘乎所以,羼杂一些恶毒的诅咒,又往往在并不可笑的时候怪怪地笑起来,使我觉得他有点心理变态。可是他还是保持着警觉,在经过一个小村庄时,我想引他进去以便找机会逃脱,他一把拉住我,从村边绕了过去。我想,他之所以和我走了这么久没有动手,说不定是因为他需要倾诉,几年来他可能从来没有机会向人倾诉一下自己的遭遇,他其实是一个苦闷的人,一个没有听众的人,积聚了太多的痛苦、仇恨和愤怒。人总是这样,喜欢将自己的不幸转嫁到别人头上。谁会想到,那个与我毫无关系的女人,竟会害得我这样惨。
我真的饿了,又提出吃消夜。他很为难地东张西望,说,这里没什么小店,这里太偏僻--怎么不知不觉就走了那么远呢。我想,这不是你故意找的地方吗,还说不知不觉,好像我们谈得多投机似的。我说,我们回城去吧,吃碗面条什么的。他稍一犹豫,说,再走一程,反正明天不用上班--你真的很饿?我不能急,一急容易露出马脚,只好说,没关系,克服一下吧。
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身上有点凉,可我不敢坚持回去,怕他起疑心。他在我耳边夸耀着他做菜的功夫,说我们以后可以开个小吃店,还说先要让我好好尝尝他的手艺,当然,他说,长久没做菜了,先得温习温习。他抓住我的手,拿到眼前看着,迟疑地说,这戒指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说当然是真的,怎么会是假的?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我补充说,这是一个男人送的。我没有骗他,这是我丈夫送的。他说,扔掉,我自己会送,不但有戒指,还有项链。这个戒指扔掉吧。我说扔掉是不必扔掉的,去换钱吧。他说,对对,我有七条项链、十二只戒指,我也不送给你了,都去卖掉,先把你家里的债给还掉。
是金的吗?
有金的,白金的也有。他搂着我的腰,吻我的脸。他身上的烟味和霉味刺激我的鼻子,差点打喷嚏,他嘴里还有一股极淡的洋葱味,我想起鬼有洋葱味的传说,不过并不怎么恐惧,只是颇为恶心,非常想喝水。他接着说,不对不对,我们先不还债,帮你弟弟读完大学,那时还怕还不出?我再也不干这事了,你也不可再做那种事,都金盆洗手,做点小生意,赚点钱,过日子。我低声说,当然好,就怕你又会半夜里出来。
不会不会,他说,我发誓不会,谁愿意每天提心吊胆的?我只是不知日子怎么打发,才这样子,再乱来,天打雷劈。我忙伸手捂住他的嘴巴,叫他不要发誓。我的动作可真经典我想,像演电影似的,搞得温情脉脉。
他看上去很高兴,嘴里不停地说着什么,不说话时就哼歌,哼了半段又跳到另一段,却听不出哼的是什么曲子。他身上发出的霉味弄得我心烦意乱,全身发痒。前面朦朦胧胧的有一片灯光,让我心情紧张,希望到了那里,我能靠它摆脱这个男人。但我知道,这只怕也只是如意算盘。
灯光已经照射到我们身上,我的连衫裙的颜色也能够约略分辨出来。我看出那是一个小火车站,有几个人影在站台上晃动,大概在等火车。小卖部里面陈列的各色商品,凭着想象似能远远看到,而且色彩非常诱人。我们竟已走了那么多路。
他拉住我停下来,看着那些人影,说,我们不过去,这里挺好的,坐一会吧。我说,我想吃东西,我老早饿了。他很不自然地笑笑,在铁轨边的水泥地上坐下来说,稍微等会儿,我想等会儿。我说,那你等在这儿,我自己去买,我实在饿了。他拉着我坐下,说,我会去买的--怎么能让你去买?不过等一下,等火车过了再去。
我知道他害怕那些人,害怕人群,也就是说他对我还怀有戒心,他并不信任我。对他来说,刚才我们谈论的一切,他是很愿意相信的,仅此而已。
汽笛声吓了我一跳,火车从我们身后过来。我突然想到我可以乘他不注意,跳过铁轨,在火车的掩护下逃走。这个主意让我惴惴不安,呼吸急促,心怦怦直跳。我想机会终于来了。我两腿颤抖着无法自制,手心发热,去摸包里的西瓜霜含片。
火车头呼啸着冲过我们身边,我松了一口气,心还在剧烈地跳着,偷偷瞥了他一眼,生怕他看出我刚刚流产的企图。在车厢射出的灯光中,我看到他长得还挺俊,脸上轮廓分明,两道浓黑的眉毛紧紧压着眼眶,两眼却显得小了些,还怕冷似的往鼻梁挤压,两颊又过于开阔,整张脸上布局就有些局促。我还是第一次看清他的样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目光柔和,似有一种平安喜乐的恬静。火车的灯光在他脸上移动变幻,他的身体在我眼里就有些虚无,难以捉摸,使我心里惴惴不安,仿佛即将打破一个很贵重的易碎物品,闯下大祸。他偶尔看看火车,这时他的表情会显得心事重重,像一个忧伤的送行人。火车喷着粗气,速度渐渐减慢,终于停止。车厢里有些乱糟糟,一个小孩扔出一块西瓜皮,打在他的脚边,我不知怎么的,担心他会发火,就将手搁在他的膝头。他冲那小孩笑笑,送了一个飞吻。小孩脸上还留着一粒西瓜子,将头歪来歪去,一直看着他,忽然从窗口俯身出来,朝我们的方向呸地吐了一口。
我们都没有说话。车厢里轻微的骚乱反使我产生一种奇怪的安定感,这安定感也正处于被颠覆之中,像悬在万丈深渊之上的树叶在等待一阵轻风。我将手从他的膝头收回,他似乎没有察觉,一直看着火车,直到它缓缓驶出车站。
站台上的灯在一盏盏熄灭。他们要关灯了,我这就去买点吃的,我对他说,眼睛看着他。他明白我的意思,说,我去买我去买。两手飞快地摸索着衣服上的众多口袋,动作从慌乱变成夸张,最后从裤袋里掏出一张皱皱巴巴的一元纸币。他低头看着这张纸币,好像被它吓坏了,连展开的勇气也没有。
我哈哈大笑,抢过纸币,用拇食两指捏着一角,像掇着一块尿布一般,将纸币吊在他面前,说:你这样请我的客?一个男人,这样请女士客?
他求饶地抬起头,微光中可以看到他的表情异常沮丧,脸如沙皮狗一样皱着,比那张纸币还难看。他极力想说些什么,但只是半张着嘴,像吃多了糠的鸭子从喉咙里发出几个低哑的单音节。我痛快地冷笑几声,放开手指,看着纸币掉落地上,说:一个大男人,就这样出门?算了吧,我自己买。我让他独自呆在那儿无地自容,自己迫不及待地走向站台,耳朵听着他的动静,怕他不放心或者识破我的用意,又阴魂不散地跟上来。
大概是他的自尊被撕裂的程度超过了我的估计,他并没有动。我越走越快,最后几步开始小跑,并回头看了他一眼。他一动不动地站着,连姿势也没变过。我扑上小卖部的玻璃柜台,刺目的灯光中见一个胖胖的中年女人正准备上门板,看见我很惊异地问:你……想买什么?
我喘了一口气,边掏钱,边压低声音说:有电话吗?快叫警察。
见她没反应过来,又说:你听着,别往那边看,那里有个男人,他一直纠缠着我,想抢东西,还想干坏事,请你打电话给警察。
她不自觉地探出头来,我忙低喝一声:别看!她疾忙缩回去,说:坏人?我点点头,她赶紧抓起电话,低低地说了几句,然后像被烫着似的扔掉话筒,脸色发僵,呆呆地看着电话机,好像做错了事情。
我从柜台上的塑料篮子里拿起一只面包,但喉咙发干,连塞进嘴里的愿望也没有。我回头张望,看见他十分缓慢地弯下腰,伸手到地面,大概捡起那张纸币,然后慢慢走过来,昏暗的灯光下他的身子影影绰绰。我打了个哆嗦,忙对女店主说:快给我拿一罐饮料。她吓了一跳,解释说:我已给车站派出所打电……饮料?她的手伸向货架,转过头讨好似地看着我说:哪种饮料?随便哪种,我焦急地说,随便哪种。她目光游移,小心地说:可口可乐行不行?我说:行行,快给我。我又回头看,见他已走上月台,心里一乱,来不及多想,手脚并用,爬上柜台。女店主吃惊地低叫道: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一边拚命将一听可口可乐往我手里塞。
这时从小卖部后门进来两个衣冠不整的警察,过来抓住我的胳膊将我拖进去,我的连衫裙袖子发出撕裂的声音。拖我进去的警察悄悄问:人呢?我摔进柜台里侧,右手撑着地说:在外面。两个警察又无声地闪出后门。
我站起来,探头往外一张,见那人站在月台上看我。他显然还没弄清我在干什么。突然两条人影向他迅速靠近。我看见他们伸手搭上他的肩膀,但看不到是不是同时抓住了他的手臂。三个人的身体紧靠着停顿了一会儿,两个警察忽然踉踉跄跄跌开几步。那人的手臂在空中做了个用力往两边分开的动作,还传来鞋底与水泥地面磨擦的尖利声音,跌跌撞撞地往田野里飞奔。我似乎看到他隐入黑暗时扭头看了我一眼。
这种人就是这样,我向黑暗中张望着,对女店主说,这种人就这样。我自己也不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只是感到我现在这副样子挺狼狈,可能也不是因为这个,而是他回头看了我一眼,而我觉得那是极其危险的眼神,所以我挺害怕,想找点儿话说。
女店主谨慎地从我手里抽出五元钱,好奇地问:你怎么碰上他的?
我整理着连衫裙袖子的裂口,心想,我都干了些什么呀。我以后深夜出门,会不会又遇到他?他再也不会放过我了,这种垃圾,只怕谁也不会放过了。我带着哭音对女店主说:这种人就是这样,这种人……我见得多了,一不小心就缠上你……他就会逃跑,他逃不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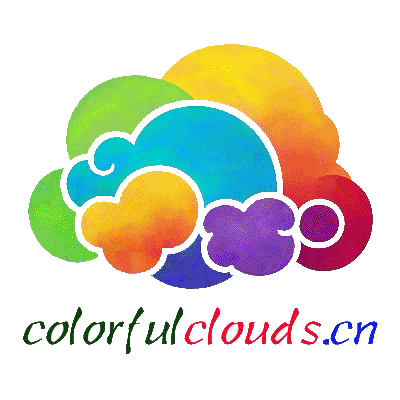
|
只是碍于老同学的情面,我才接下这个离婚案子的。下决心离婚的那个女人是我同学的远房表姐,据说挺漂亮,曾是什么学校的校花或哪个局的局花。她就住在紫石宕小区的边缘,离我家不算远。紫石宕事实上是城北的统称,包括北郊和部分城区。在我们城市,对住在紫石宕小区的人普遍缺乏好感,昔日那里曾聚居着本地的显贵,随着城市重心的转移,现在几乎已沦落为城市贫民的集中地了。我之所以辞职转行,在内心深处恐怕也与此有关,希望积聚一点财富,以便将来能搬到远离紫石宕的新区去住。
晚饭后我换了套淡黄色的连衫裙,带上黑色的小挎包,在紫石宕河北边的小路上散步。天色阴阴的,西天乱叠着一些淡红的云霞,空气稍有点闷。铁路那边的西瓜田里,有几个人围在一起高声谈论,旁边的小卡车装满了西瓜。看见我,一个光头青年打了个唿哨,做着吃西瓜的动作,还怪模怪样的啧味道,别的人都哈哈大笑。我自然不予理睬,沿铁路走了半个多小时,过桥回到城区,从紫石宕路步行去同学的表姐家。
如我所料,我的当事人情绪激动,没说两句就哭哭啼啼起来。这种场面我见得多了。我感兴趣的是重大经济纠纷,最烦的就是这类事。但既然来了,我只好一边在心里抱怨老同学,一边对她的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一边了解情况,调查取证。她的故事无非是这样的:那个她倾心爱着的丈夫捞到一官半职后,就开始在外面寻花问柳夜不归宿,导致感情破裂,他甚至转移家庭财产,暗中作好撤离婚姻的准备。他当然同意离婚,但要取得孩子的抚养权。她在叙述中还多次提到她的表弟的名字,似乎这个名字是一个符咒,能让我的同情心和工作能力都加倍。其实我此刻心里最恨的就是她那位胡乱介绍案子的表弟,而且她那种事我见得多了,依我的想法,放弃孩子抚养权,争回点财产就得了,像她这样容貌不恶的女人,没有孩子的拖累,说不定还能找个不错的丈夫。但她一定要孩子,态度坚决到咬牙切齿的地步。一个女人能退守到哪里?只能到孩子为止。这我理解,心里就有点儿不好受。这样的事我确实看得多了,但总会使我难受。其实打动我的不是她那种可悲的遭遇,而是她的痛苦。
那个被争夺的孩子是个阴沉的小男孩,十一二岁光景,他闷闷不乐地看完动画片,就开始拆一辆玩具汽车,将零件扔得满地都是,有一个轮子还飞进了我的茶杯。他吃了母亲的一个耳光后,一声不响地躲进自己的小房间里去了。我发现他的眼神对我充满敌意,似乎是我使他的家庭面临破裂局面的。这孩子自己愿意跟谁过日子呢?我想他当然希望选择与父母一起过,但他的父母不让他这样选择了,他的选择多不自由啊。
她哭哭闹闹,又是诅咒又是发誓,直弄到深夜11时事情才算告一个段落。我起身告辞,她收起泪送我到门口,又紧紧拉住我的手,恳求我无论如何要帮她将孩子夺到手,说孩子若跟着那样狼心狗肺的人过,也非变成狼心狗肺不可,长大了不知道会害了多少人。没说几句又声泪俱下起来,好像看到了她儿子不妙的前景。我急于回家,并没有被她这种深谋远虑折服,当然也没有摔脱她的手,只是劝她多多保重,顾眼前要紧,劝得我自己也鼻子发酸。这样又说了半个小时,我才得以脱身。
我二十岁左右那会儿,这条幽静的紫石宕路在小城的年轻人中很出名。那时候我们城市只有几个规模很小的路边公园,紫石宕路比那些小公园撮成了更多的婚姻,一对青年男女在这条路上走,就意味着他们在走向婚姻,至少是他们有这种企图。所以它有个冗长的别名叫做“一千五百米爱情线”。现在它和紫石宕小区一起没落了,显得更加幽静。城市向三个方向拓展,唯独不在这个方向蚕食农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路上我走得很慢,我可不想将心烦带回家里。我不是个工作狂,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当妻子和当律师同样重要,不能搅在一起,更不能颠倒。这是我一贯的原则。当别人称赞我办事干练得体什么的,我以为可能正是由于这样的处事方式。我有一个朋友,是小学教师,她做事正好相反,常常将作业本带到家里批改,这肯定影响生活,我担心她有朝一日会忘乎所以地在教室里结毛衣或剥蚕豆,或者对着丈夫讲解课文。所以我至少在回家的路上要将工作都打理一遍,放置在脑子的某个角落里,暂时不去管它。这不难。毕竟是深夜,行人很少,偶尔也有人骑着自行车超过我,在残缺不全的路灯光下,他们的影子像幽灵似的忽明忽暗,好像是从路边一个无形的屏幕上经过。有两三个骑车的人还回头看了我一眼。我知道他们可能是将我当作那种女人了。这使我很恼火,我猜想他们用的眼光可能是下流的、憎恶的,也可能是同情的,不管是哪种,都使我恼火,就在心里驳斥他们的眼光,举出与那种女人的许多种区别,所以直到经过城市边缘紫石宕河上的虹影桥时,才发现有人不知什么时候跟上了我。那人的脚步很轻,几乎有点儿蹑手蹑脚。我不希望学过的防身术真的派上用场,心想他也可能不过是碰巧和我同路,但我还是心情紧张,不由得呼吸急促,加快脚步。后面的脚步声也急促起来,并渐渐接近。
路的左边隔着围墙是一排排灰色的楼房,毫无生气地隐藏在夜色里,每扇窗子都黑黑的。右边是发臭的河,路与河之间是一排叶子过于密集的梧桐树,河那边的田野、村庄和铁路,在黑暗中无法看清,只有虫子的鸣叫声不停地传来。我的高跟鞋着地发出响亮的声音,在寂静中分外刺耳,好像在与身后的脚步声作虚张声势的争辩。
我偷偷试演了一个防身招术,发现动作僵硬生疏,双臂根本不听使唤,两只手掌却不自觉地微微颤抖,手心也已经热得发潮。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也越来越轻,简直是踮起了脚尖,每一声都像踩在我的心上。我脊背上的汗毛像草一样蓬勃竖起,草尖触到那一大团悬挂在背后的黑暗,让人心里阵阵发虚,觉得再也没有勇气相持下去。我一边想象着自己猛回身抡起挎包尖叫着摔出去的情形,一边偷偷回头瞥了一眼,不禁在心里打了一个突:身后空空荡荡的,根本没有人,连影子也没有,只有一条路,还有风。这远比看见一个相貌凶恶的歹徒更使人毛骨竦然,我全身有些发软。道路在微明的灯光下难以分辨,灰蒙蒙的,虚假得像模糊的碳精画。沙沙作响的风吹得我直打寒颤--我已满身冷汗,感到四周有无数双眼睛在偷看。
我定了定神,努力地笑笑,从容不迫地慢慢回头。就在这时,我眼前一黑,一只大手无声地搭上我的肩头,我的心突地一跳,一口冷气噎住了喉咙,接着看见一个高大的人影紧靠着我站着。他一声不响,脸也无法看清,身上发出一股混杂着霉味和烟味的奇怪气味,他的手捏得我肩膀发痛。我感到浑身乏力,虚脱了一般,喃喃地说,你想干什么?声音嘶哑飘浮,听上去像梦中的乌鸦叫声。他的喉咙里发出喀喀的声音,我没有听见他说话,又问,你想干什么?
一道亮光掠了过来,他反应迅捷,一把按住我的后脑勺,将我的脸用力按在他的胸口。我毫无防备,也不明白他想干什么,只闻到他衬衫上的一股霉味,然后就呼吸不出,脑袋混混沌沌,好像还听见有一辆车从身边驶过。我的挣扎就像蜻蜓撼石柱,丝毫不起作用。他突然放开我的后脑勺,我的脑袋不自禁地向后一仰,身子差点失去平衡。他抓紧我的肩顺势往路边带了几步,一只手粗暴地摸索我的手腕、手指和脖子,并扯住我的项链,另一只手抓住我的挎包。我的神志有点清醒过来,意识到面前是一个男人,而且是一个抢劫财物的歹徒,忙抓紧挎包,用拳头打他的手,急促地说:
带子要拉断了,带子要拉断了。
我不明白此时我最关心的为什么竟是挎包的带子。我学过的防身术毫不管用,既施展不出,也没想到要施展一下。
你说什么?他愣了愣,问。
也许与我那专门与人比赛说话的职业有关,听到他开口说话,不知怎么的心里就不大害怕,并很快镇定下来。我想,语言是一种武器,而我这方面的武器应该是比较精良的,我又想,他犯了一个错误,他说话了,这等于授我以柄。我壮起胆用劲掰他的手指,随口说道:我不喜欢这样的,你不知道,我不喜欢这样的,你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不知道?我感觉到他抢夺的动作缓慢下来。
我第一个想法是告诉他这是犯法的,并用我的律师身份威吓他。但我马上否定了,因为这只会使他害怕,人在害怕的时候容易铤而走险,说不定就对我下毒手。他是一个男人,当然有男人的弱点,所以我用一种假装害羞的口气说,我不喜欢这么快……这么快……我努力微笑地看着他的脸,一点儿也不向周围张望。跟你说吧,我与别的姑娘不大一样,不喜欢很快很直接的,太像做生意。
他抓着我的挎包,没有说话。我知道现在最危险的是沉默,只能继续假装不明白他的险恶用心,不停地说丰话,同时习惯性地从包里取出一片西瓜霜含片噙在口里。我明白即使我失身了,他还是会抢走我的所有东西,说不定还会杀了我。我得尽量拖延时间,分散他的注意力,否则一点机会也没有。虽然他看不清楚,但我还是又给他做了一个自以为灿烂的笑容,说,可能你不大习惯,可我想总得互相有个了解,找点情调,否则算什么啊?我轻轻抓住他的手,小心翼翼地移到身侧,让他挽住我的胳膊,征求他的意见:我们散一会儿步好不好?
他看上去有点拿不定主意,说,你甭想玩花样,这没用。
你怕我玩花样?我笑得弯下了腰,指着他说,什么花样?怕我吃了你?胆子那么小,白长那么大个儿!我挽着他慢慢移动脚步,你从不这样的?先散步,吃点消夜什么的,你怎么从不这样?干什么都得有个次序。
废话少说!他又开始在我的脖子里摸索。他是想找到项链的扣襻。我吃吃笑着,声音干涩,一边轻轻拨开他的手,说,心那么急干什么?一点情调也不懂,算什么男人?过去你和几个女人好过?
他生气地说,我像那样的人吗?我从不乱搞!
那今天怎么有兴致出来?我说。我意识到谈话的方向有点危险,如果他放弃接受女色的诱惑,很可能马上着手抢劫,那我就没有机会了。我们先去哪里吃点东西?
不吃。他说,我不饿。
可我有点饿了,你陪我去吃点儿吗。
我不饿,你也不饿。他说着短促地笑了一声,听上去像一颗石子掉落在地,立刻又用凶恶的口气说,别动脑筋了,没用的。
左边的围墙尽头是一个小弄堂,一缕灯光从弄堂口投射到这条路上,将路截成了两段,另一段隐没在黑暗中。那盏灯看上去比紫石宕路上所有的路灯加起来还亮。我侧过身子缓缓地向灯光走去。他似乎识破了我的用心,粗暴地拉住我,继续沿着紫石宕河走。经过弄堂口时他明显地快走了几步。灯光在我们身上一晃而过,我只来得及瞥见他有一张微黑的中年人的脸和一头乱糟糟的头发,眼角的余光似乎还看到他的西装是灰色的。我沮丧地想,如果我不是存心看他的脸,说不定还能看到更多的特征呢。
在我们这个不大的城市里,我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却窝窝囊囊地假扮成一个妓女被这下三滥的恶棍挟持,实在令人哭笑不得。现在我们行走的方向与我回家的方向一致,这多少给了我一点信心。只要到家门口就好办了,到时我要给他点颜色看看。被我送进监狱的人还少吗。但此刻我不敢掉以轻心,一个劲地说着话。我编了个故事,说我家里因为火灾欠下一大笔钱,还有一个读中学的弟弟和生病的母亲要供养,只好跑到外面来打工挣钱,没想到找工作这样难,身边的钱用光了,不得已干起这一行。我希望能用这个老套故事骗得他良心发现。
他没有出声,一边走路,一边用身体将我挤在河的一侧,右手绕过我的背部用力抓着我的右臂。我不知道我的故事是不是对他发生了作用,偷偷地看他的表情,但天太黑,只看见他脑袋的轮廓。他注意到我在看他,用低沉的声音说,你这种故事我早就听见过了。很多人都讲这样的破故事。他的右手放开我的手臂,接着一个锐利的东西顶住了我的腰部。他说,不许叫,一叫就没命。我吃惊地问,你干什么?话才出口就明白了,后面有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过来了。那是个小伙子,穿着一件白衬衫,超过我们时不经意地扭头看了一眼,又哼着歌继续赶路,自行车骑得飞快。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黑暗之中,心里升起一种苦涩的滋味:这个陌生小伙子,他根本不知道他也许是我唯一的救星。我又想,这个恶棍的耳朵倒蛮灵的,我怎么没听见声音呢,看来他确实挺难对付。这时我才突然发现:他根本没有相信过我的任何一句话,他听着我说话,和我一起走着,却半点也没相信过我,也就是说,他有自己的打算,他要拿我怎么办?如果他是一个惯犯,过去他拿别的人怎么办的?我想起先奸后杀,洗劫财物,分尸沉江等词语,但那样的可怕情形,却怎么也不敢想。
这个城市睡得好熟啊,我想,白天熙熙攘攘的人群,现在都分散到各自的家里安安稳稳地睡着,包括我的那个同学,他搂着他的妻子进入了梦乡,却没想到我快被他害死了。他的该死的表姐离婚关我什么屁事?我心里一阵气苦。
你这是干什么?我恨恨地说。
我只想让你放老实一点。他嘿的笑了一声。
什么东西,扎得我好痛。我用手摸了一下,受了惊吓般说,刀子,你拿刀子干什么!你是黑社会的是不是?你认不认识雷司令?
他妈的,你才是黑社会。
我知道了,你出来想买西瓜,没买到西瓜,就想找女人玩,你这种人我知道。
不是,我就爱带刀子,你怕了?
你收起来吧,这东西又不好玩。
他没有收起来,刀尖扎得我一痛一痛的,走路倒像是受刑。我想我穿上一件罩衫出来就好了,我本来应该想到的,初秋的深夜天气会变冷。紫石宕小区已远远抛在后面,通天桥已经过去,罗家桥新村的围墙也走完了,只有紫石宕河还在我们的左侧发臭。
三里亭新村到了。第四幢楼房的303室就是我的家,丈夫在家里等我。我不回去他是不会睡觉的。我注意到我家的窗口透出明暗变幻的光线,他在看电视。他真是好耐心啊,妻子那么晚还没回到家,他居然还有心思看鬼电视。他不会到窗口来张望一下?我与一个高个男人在路上搂着散步,他难道不在乎?我晚上出门,他应该陪我去才对,要不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狼心狗肺的东西,你窝在家里等吧,等我的尸体吧。
我的家就这样很快很平静地过去了,平静得连我自己也难以置信。我想,我这和在自己家门口被人劫持有什么两样?原来生活是这样的不安全。
前面是环城东路。到了环城东路,我总该有机会了吧,我想,那里肯定有人的,只要熬到环城东路,一遇到人我就挣扎叫喊,即使被他扎上一刀,也得逃脱他的魔掌。不然的话,谁知道他会带我到什么鬼地方去。环城东路,霓虹灯美丽动人,街灯的光芒明亮地交织着,那是我即将到达的天堂。我的脸上发热,脚步因兴奋而加快,心悬在喉咙口,几乎要蹦出来。他忽然捏住我的胳膊用力一推,我猝不及防,踉踉跄跄地几乎摔倒,发现已被他拉着拐入一座小木桥。我胸口一沉,一股寒意冒上心头,头皮发麻,脑袋晕乎乎的,身不由己地跟他越过紫石宕河。紫石宕河这条城区和农村的分界线,现在成了天堂和地狱的分界线,我知道,走过这座桥,我是死定了。我挣扎着说,你这人,怎么能……这样?他坚硬如铁的手又紧了紧,说,你不是想要情调吗?这里情调不错吧?我苦笑着说,不过我不喜欢……不喜欢在野地里……他打断我的话,你想到人多的地方是不是?你想叫别人来抓住我是不是?
脚踩着田塍上的草丛,发出细细的沙沙声,旁边有一匹小动物窜过,钻到一个黑乎乎的草堆里去了。我叹了口气,说,我从来没有被人带到这种地方来过。我想起我编的那个故事,又说,我在老家也有个男朋友,我们只是去镇上看两场电影,从来不去野地里。不过有的人是去的,比如我的一个好朋友,她和男朋友第一次好就在野外。
你和男朋友第一次好呢?他干笑着说,难道在旅馆里?我呸了一声,你胡说什么呀?唉,我们还来不及好,我家里就着火了,后来他就不理睬我了,就是我约他去看电影,他也总是推三阻四的不肯去。我有时想,如果我答应他,给了他,他会不会不理我。不过也无所谓,男人总是这样朝三暮四的。他哈哈大笑,说,人总是这样,你怪我我怪你,依我看,如果男人是朝三暮四,女人就是水性杨花,都一样的。
我低着头慢慢走着,沉思了一会儿,小心翼翼地说,你的老婆,你的老婆也水性杨花吗?他用力搡了我一把,大声骂道,放屁!你他妈的才是水性杨花的婊子!我拐了一下,摔倒在路边,委屈得哭出声来,我从来没被人这样骂过,这狗娘养的居然敢这样骂我!我拿出手帕擦着眼泪,提高声音说道,你这姑娘养的私生子,我愿意水性杨花吗?我不想好好地嫁个人过日子吗?我愿意家里着火吗?我爱当婊子吗?我坐在地上用力蹬着两腿,妈妈啊,你这该死的生我出来干什么?这世界婊子还不够多啊?我一边撒泼哭嚎,一边心里诧异:我竟还有这一手,演技不错啊,原来当泼妇这么容易,说不定每个女人身上都有泼妇的影子吧。
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弯腰拉我起来,说,好了好了,不要哭了,算我不对。我收住泪,小声说,你以后不可以再骂我的。他说,不骂不骂。
我们像一对重归于好的恋人一样并肩走着,我望着他的侧影说,你的脾气很好啊,你老婆会对你不好吗?他嗡声嗡气地说,谁说她对我不好?我冷笑一声,那你为什么跑出来偷荤?你这小没良心的。他厉声道,别说了!你不要生气嘛,哎,如果你没有老婆,会不会娶我?
什么?他吃了一惊,娶你?
对呀,我嗲声嗲气地说,不过你别笑,我知道你不会娶我的,像我这样的人,唉,我这辈子是没指望了,做过这种事,能嫁给谁啊。
我以为他会说“当然会娶你啊”之类的话与我开开玩笑,可是他没说,摸索一会儿,用火柴点上一支香烟,一边抽着,一边低着头走路,我甚至能感觉到他阴沉着脸,还在动着什么坏念头,心又开始怦怦乱跳。这时我突然发现我犯下一个弥天大错,我的包里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东西,就是连白金项链、金戒指全被他抢走,也不过值两三千元钱,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我却为了这一点点东西,落到了这样的危险之中,这简直是个黑色大幽默!我想起我经手过一些案例,有两个老头打麻将,为了争五元小钱,竟闹出了人命;还有一个人,不愿买两毛钱的公园门票,翻墙进去时掉下来,落得个终身残废,状告公园,又赔出诉讼费。我现在与这些人又有什么区别呢?我如果被他抢走一点什么,趁他不备一边逃一边喊救命,他胆子再大也不敢再追我吧。现在,我将自己扮成妓女,还自鸣得意,以为骗倒了他,却在不知不觉中身陷万劫不复的境地!明天人们发现我的尸体的时候,恐怕谁也不会想到,是我自己放弃了逃生的机会。我满心说不出的窝囊和后悔,都变成了满腔怒火,恨不得立时死掉才好。
我知道,你本来是个好姑娘。他犹豫着说。
放你妈的臭狗屁!我心情恶劣得像填了一肚子稻草,尖声叫道。
怎么了?我又说错了?他惊讶地说,我没有要讽刺你的意思,真的没有。
你有,你有,我大喊道,你讽刺挖苦,偏偏我根本不是你想的那种人,不是什么野鸡,我告诉你,我是一个律师!我的声音突然中断,“律师”两个字像一枚突然爆炸的炸弹,震得我耳朵嗡嗡直响,我感到一阵晕眩。我又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一认清我的真面目,用那双坚硬的大手对付我脆弱的脖子,不要五分钟就能叫我断气。
我知道我知道,他说,你当然是律师,你是个顶呱呱的律师。
他知道!怪不得他根本没相信过我的话,其实他早就知道我是谁--说不定他是某个被我送进监狱的罪犯,或者是罪犯的亲戚朋友,他是来报仇的,他碰上我不是偶然,而是蓄谋已久。他带我到这种偏僻的地方,居心险恶不言自明,他要怎样折辱我杀害我,也已策划得周周到到。我身子一软,倒了下去,脑袋里一片空白。
他及时扶住了我,阴恻恻地说,小心,这路不大好走。你知道我是谁?他搂着我的腰肢说,我是一个飞行员,开喷气式战斗机的飞行员。他停住脚步,拨动我的身子,让我面对着他,继续说,小孩子懂个屁……全不是这么回事,活着就是你想去什么地方,却偏偏让你往相反方向走,这我老早就弄明白了。
你是飞行员。我头冒虚汗,低着头抽泣道,你是真的飞行员。
不是,飞行员现在在天上,打着红灯绿灯黄灯,在天上飞,他笑起来,说,这话听上去像傻瓜。如果我真当上飞行员,说不定做人也一样没意思。
天上飘下零星小雨,落到脸上凉凉的。一只蝙蝠从头顶无声地掠过,在微茫的天光中能看到柔软的长翅展开着。天上没有飞机,也没有星星,只有城区的各色灯光,寡淡地涂抹了半边天空。虫子的叫声远远传来,听上去有一种压抑的热闹,令人不快。这时我们已经上了铁路,沿着铁路线走。怎么没意思呢?你做人也会没意思?
你刚才说过你愿意嫁给我是不是?你说过的。他又站住,面对着我说。
我知道你要笑话我,不许……
你说过的,是不是?你再说一遍。
好好好我说我说,我嘻嘻笑道,我愿意嫁你。
我知道你不是真的,他哈哈笑着说,我知道,我知道的。
当然不是真的,你当是真的?我奇怪地说,你有老婆,我有老……婆,再说,我是个这样的姑娘,你即使没有老婆,怎么会要我?
如果我没有老婆呢?
我突然意识到什么,心扑嗵一跳,从包里摸出一片西瓜霜含片塞入嘴里,用认真的口吻说,你真的会娶我?我不信。我不是自卑,你在玩我是不是?你在玩我。唉,像我这样的人……
你要怎样才相信?我是挺严肃的。
可我总觉得高攀不上……你不想我们再了解得深一点?这事太重大了。
他揽住我的腰,在我的额头轻轻吻了一下。他的双眼注视着我,在黑暗中发出一种黑光。沉默了一会儿,他说,你知道我这么晚了出来干什么?我不是来找乐子的,我是来抢东西的。
我啊地叫了一声。我知道他是来抢劫的,但没有料到他会自己说出来,在谈论那样的话题时突然之间说出来。他这就要跟我摊牌了!要动手了!我惊恐地看着他,结结巴巴地说:你怎能……怎能……
他打断我,飞快地说,你放心,我以后决不再抢了,做这种事,运气再好也会有失手的一天,我不会再做了。我们就过穷日子,找份工作,想办法帮你还债,供你弟弟读书,不过你也不能再做这种生意,你说好不好?可是……你老婆……
我确实没有老婆,他的手在空中虚劈了一下,我老婆跟我离婚了。她嫌我没出息,总是被人欺侮,我在单位里他们叫我什么?叫我糯米团子。他短促地笑了一声,我糯米团子,他们他妈的才是糯米团子呢,他们敢半夜里出来抢劫吗?嗤!他忽然激动起来,一边大步走着,一边说,我连白脸狼的老婆也抢过,白脸狼这狗娘养的,就会扣我工资,对人家说,扣吧,扣糯米团子吧,他屁都不敢放一个。他是狗娘养的,他跟老婆都被我抢了,他倒是屁都不敢放一个,你猜我怎么干的吗?我摘下她的项链戒指,掏空她的口袋,还当着那狗贼与他老婆亲了个嘴,他屁都不敢放一个,真他妈过瘾。我是糯米团子吗?我怕什么?我早两天就辞职了。他微仰着头,眼睛里闪着绿荧荧的光,脸上似乎还有笑容,黑暗中看不大清楚,显得很可怖。
白脸狼……没有报案?我迟疑着问。
不知道,他不敢报,我叫他蹲下,他乖乖蹲下,屁都不敢放一个。
为什么不敢报?
他愣了一下,忽然发起脾气,报他妈的大头鬼,我没强奸他的婊子老婆还算客气,他们一家人都是婊子!我操他十八代祖宗姥姥!突然顿住,呆了呆,说,我以后肯定不干这种事了,你要相信我,我老婆跟我离婚了,我想我完了……他歪过头看着我说,你问那么多干什么?你再多嘴看我掐死你,你以为你是谁?
我吃了一惊,退后两步,在铁轨上绊了一下,大着胆子说,人家只是怕你出事嘛,你那么凶干什么?认识你第一天就这样,我宁愿被你掐死。
我只是想起一些事,挺窝心的,他叹了口气说,我过去对老婆百依百顺,可她不知足,她总是不知足。离婚后我的生活一团糟,连工作也丢了--我要杀掉她,反正我也已被她害惨了,同归于尽吧,我要杀--当然了,现在不同了,我已懒得理睬她了。
他的故事几乎和我编的故事一样流行,他说他和妻子是中学同学,结婚后生活平淡,也没有孩子。后来妻子有了外遇,打算将那个第三者变成第二者,便开始有计划地与他吵闹打架,然后每天冷战,然后分居,最终离婚。她从来没有对我好过,他说,她从来只顾自己的。那个女人几乎搬空了家里所有东西,只留下一套两居室的房子。他感到非常绝望,每天关在徒有四壁的家里痛不欲生。他分析说,现在想起来,如果说他爱妻子真爱到这程度,那也不见得,他只是感到被彻底抛弃了,就自暴自弃。被一个女人抛弃,就是被全世界抛弃,这种情形下男人是看不到一丝希望的。他也没什么朋友,如果有朋友陪伴,说不定不会变成这样子。
总之,他像生活在黑暗深处,心情恶劣,神经衰弱,常在深更半夜出门,在街头徘徊游荡。有一天夜里遇到一个问路的女子,他想也不想抢走了她的坤包,那时街灯明亮,行人不少,那女子似乎被吓傻了,站在那里看着他消失在一条小巷里。这是他的第一次抢劫,事后想想对自己的胆大妄为尚有余悸,以为第二天会有满城警察追捕他。实际上他早将坤包丢在一个阴沟里,根本没有打开看过。但他的内心深处却感到一种隐秘的喜悦,似乎对妻子作了一次程度轻微的报复。这种报复以后多次发生,渐渐成了一种习惯。
没多久,这成了他的生活来源,白天睡觉,晚上出来游荡,生物钟也颠倒了,晚上无法合眼,面对空空的墙壁感到难以忍受。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出来后本想找个工作,可一连碰了三个灰鼻子,就索性重操旧业。
这个乏味的故事他讲得支离破碎,有时忘乎所以,羼杂一些恶毒的诅咒,又往往在并不可笑的时候怪怪地笑起来,使我觉得他有点心理变态。可是他还是保持着警觉,在经过一个小村庄时,我想引他进去以便找机会逃脱,他一把拉住我,从村边绕了过去。我想,他之所以和我走了这么久没有动手,说不定是因为他需要倾诉,几年来他可能从来没有机会向人倾诉一下自己的遭遇,他其实是一个苦闷的人,一个没有听众的人,积聚了太多的痛苦、仇恨和愤怒。人总是这样,喜欢将自己的不幸转嫁到别人头上。谁会想到,那个与我毫无关系的女人,竟会害得我这样惨。
我真的饿了,又提出吃消夜。他很为难地东张西望,说,这里没什么小店,这里太偏僻--怎么不知不觉就走了那么远呢。我想,这不是你故意找的地方吗,还说不知不觉,好像我们谈得多投机似的。我说,我们回城去吧,吃碗面条什么的。他稍一犹豫,说,再走一程,反正明天不用上班--你真的很饿?我不能急,一急容易露出马脚,只好说,没关系,克服一下吧。
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身上有点凉,可我不敢坚持回去,怕他起疑心。他在我耳边夸耀着他做菜的功夫,说我们以后可以开个小吃店,还说先要让我好好尝尝他的手艺,当然,他说,长久没做菜了,先得温习温习。他抓住我的手,拿到眼前看着,迟疑地说,这戒指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说当然是真的,怎么会是假的?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我补充说,这是一个男人送的。我没有骗他,这是我丈夫送的。他说,扔掉,我自己会送,不但有戒指,还有项链。这个戒指扔掉吧。我说扔掉是不必扔掉的,去换钱吧。他说,对对,我有七条项链、十二只戒指,我也不送给你了,都去卖掉,先把你家里的债给还掉。
是金的吗?
有金的,白金的也有。他搂着我的腰,吻我的脸。他身上的烟味和霉味刺激我的鼻子,差点打喷嚏,他嘴里还有一股极淡的洋葱味,我想起鬼有洋葱味的传说,不过并不怎么恐惧,只是颇为恶心,非常想喝水。他接着说,不对不对,我们先不还债,帮你弟弟读完大学,那时还怕还不出?我再也不干这事了,你也不可再做那种事,都金盆洗手,做点小生意,赚点钱,过日子。我低声说,当然好,就怕你又会半夜里出来。
不会不会,他说,我发誓不会,谁愿意每天提心吊胆的?我只是不知日子怎么打发,才这样子,再乱来,天打雷劈。我忙伸手捂住他的嘴巴,叫他不要发誓。我的动作可真经典我想,像演电影似的,搞得温情脉脉。
他看上去很高兴,嘴里不停地说着什么,不说话时就哼歌,哼了半段又跳到另一段,却听不出哼的是什么曲子。他身上发出的霉味弄得我心烦意乱,全身发痒。前面朦朦胧胧的有一片灯光,让我心情紧张,希望到了那里,我能靠它摆脱这个男人。但我知道,这只怕也只是如意算盘。
灯光已经照射到我们身上,我的连衫裙的颜色也能够约略分辨出来。我看出那是一个小火车站,有几个人影在站台上晃动,大概在等火车。小卖部里面陈列的各色商品,凭着想象似能远远看到,而且色彩非常诱人。我们竟已走了那么多路。
他拉住我停下来,看着那些人影,说,我们不过去,这里挺好的,坐一会吧。我说,我想吃东西,我老早饿了。他很不自然地笑笑,在铁轨边的水泥地上坐下来说,稍微等会儿,我想等会儿。我说,那你等在这儿,我自己去买,我实在饿了。他拉着我坐下,说,我会去买的--怎么能让你去买?不过等一下,等火车过了再去。
我知道他害怕那些人,害怕人群,也就是说他对我还怀有戒心,他并不信任我。对他来说,刚才我们谈论的一切,他是很愿意相信的,仅此而已。
汽笛声吓了我一跳,火车从我们身后过来。我突然想到我可以乘他不注意,跳过铁轨,在火车的掩护下逃走。这个主意让我惴惴不安,呼吸急促,心怦怦直跳。我想机会终于来了。我两腿颤抖着无法自制,手心发热,去摸包里的西瓜霜含片。
火车头呼啸着冲过我们身边,我松了一口气,心还在剧烈地跳着,偷偷瞥了他一眼,生怕他看出我刚刚流产的企图。在车厢射出的灯光中,我看到他长得还挺俊,脸上轮廓分明,两道浓黑的眉毛紧紧压着眼眶,两眼却显得小了些,还怕冷似的往鼻梁挤压,两颊又过于开阔,整张脸上布局就有些局促。我还是第一次看清他的样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目光柔和,似有一种平安喜乐的恬静。火车的灯光在他脸上移动变幻,他的身体在我眼里就有些虚无,难以捉摸,使我心里惴惴不安,仿佛即将打破一个很贵重的易碎物品,闯下大祸。他偶尔看看火车,这时他的表情会显得心事重重,像一个忧伤的送行人。火车喷着粗气,速度渐渐减慢,终于停止。车厢里有些乱糟糟,一个小孩扔出一块西瓜皮,打在他的脚边,我不知怎么的,担心他会发火,就将手搁在他的膝头。他冲那小孩笑笑,送了一个飞吻。小孩脸上还留着一粒西瓜子,将头歪来歪去,一直看着他,忽然从窗口俯身出来,朝我们的方向呸地吐了一口。
我们都没有说话。车厢里轻微的骚乱反使我产生一种奇怪的安定感,这安定感也正处于被颠覆之中,像悬在万丈深渊之上的树叶在等待一阵轻风。我将手从他的膝头收回,他似乎没有察觉,一直看着火车,直到它缓缓驶出车站。
站台上的灯在一盏盏熄灭。他们要关灯了,我这就去买点吃的,我对他说,眼睛看着他。他明白我的意思,说,我去买我去买。两手飞快地摸索着衣服上的众多口袋,动作从慌乱变成夸张,最后从裤袋里掏出一张皱皱巴巴的一元纸币。他低头看着这张纸币,好像被它吓坏了,连展开的勇气也没有。
我哈哈大笑,抢过纸币,用拇食两指捏着一角,像掇着一块尿布一般,将纸币吊在他面前,说:你这样请我的客?一个男人,这样请女士客?
他求饶地抬起头,微光中可以看到他的表情异常沮丧,脸如沙皮狗一样皱着,比那张纸币还难看。他极力想说些什么,但只是半张着嘴,像吃多了糠的鸭子从喉咙里发出几个低哑的单音节。我痛快地冷笑几声,放开手指,看着纸币掉落地上,说:一个大男人,就这样出门?算了吧,我自己买。我让他独自呆在那儿无地自容,自己迫不及待地走向站台,耳朵听着他的动静,怕他不放心或者识破我的用意,又阴魂不散地跟上来。
大概是他的自尊被撕裂的程度超过了我的估计,他并没有动。我越走越快,最后几步开始小跑,并回头看了他一眼。他一动不动地站着,连姿势也没变过。我扑上小卖部的玻璃柜台,刺目的灯光中见一个胖胖的中年女人正准备上门板,看见我很惊异地问:你……想买什么?
我喘了一口气,边掏钱,边压低声音说:有电话吗?快叫警察。
见她没反应过来,又说:你听着,别往那边看,那里有个男人,他一直纠缠着我,想抢东西,还想干坏事,请你打电话给警察。
她不自觉地探出头来,我忙低喝一声:别看!她疾忙缩回去,说:坏人?我点点头,她赶紧抓起电话,低低地说了几句,然后像被烫着似的扔掉话筒,脸色发僵,呆呆地看着电话机,好像做错了事情。
我从柜台上的塑料篮子里拿起一只面包,但喉咙发干,连塞进嘴里的愿望也没有。我回头张望,看见他十分缓慢地弯下腰,伸手到地面,大概捡起那张纸币,然后慢慢走过来,昏暗的灯光下他的身子影影绰绰。我打了个哆嗦,忙对女店主说:快给我拿一罐饮料。她吓了一跳,解释说:我已给车站派出所打电……饮料?她的手伸向货架,转过头讨好似地看着我说:哪种饮料?随便哪种,我焦急地说,随便哪种。她目光游移,小心地说:可口可乐行不行?我说:行行,快给我。我又回头看,见他已走上月台,心里一乱,来不及多想,手脚并用,爬上柜台。女店主吃惊地低叫道: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一边拚命将一听可口可乐往我手里塞。
这时从小卖部后门进来两个衣冠不整的警察,过来抓住我的胳膊将我拖进去,我的连衫裙袖子发出撕裂的声音。拖我进去的警察悄悄问:人呢?我摔进柜台里侧,右手撑着地说:在外面。两个警察又无声地闪出后门。
我站起来,探头往外一张,见那人站在月台上看我。他显然还没弄清我在干什么。突然两条人影向他迅速靠近。我看见他们伸手搭上他的肩膀,但看不到是不是同时抓住了他的手臂。三个人的身体紧靠着停顿了一会儿,两个警察忽然踉踉跄跄跌开几步。那人的手臂在空中做了个用力往两边分开的动作,还传来鞋底与水泥地面磨擦的尖利声音,跌跌撞撞地往田野里飞奔。我似乎看到他隐入黑暗时扭头看了我一眼。
这种人就是这样,我向黑暗中张望着,对女店主说,这种人就这样。我自己也不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只是感到我现在这副样子挺狼狈,可能也不是因为这个,而是他回头看了我一眼,而我觉得那是极其危险的眼神,所以我挺害怕,想找点儿话说。
女店主谨慎地从我手里抽出五元钱,好奇地问:你怎么碰上他的?
我整理着连衫裙袖子的裂口,心想,我都干了些什么呀。我以后深夜出门,会不会又遇到他?他再也不会放过我了,这种垃圾,只怕谁也不会放过了。我带着哭音对女店主说:这种人就是这样,这种人……我见得多了,一不小心就缠上你……他就会逃跑,他逃不了吧?
上一篇:三世之赌
下一篇:『都市妖奇谈』· 我的森林——山鬼的故事